大学时代
按正规的说法,哈耶克学的是法律。①但是由于自己的主动精神,他获得了十分广博的学识,他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只想听最好的课,不管它是什么学科。对学生上课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在正式的学习结束时要对学生进行口头测验,所以许多人听课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雇一些指导老师帮助自己准备功课。哈耶克显然属于那些认为自己的教育不仅是接受专业训练的少数人。他后来说,他的教育经历使他学会了研究自己选择的题目的技能:“我们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我们知道如何获得有关一门学科的知识。我今天发现,甚至在自己的领域里声誉卓著的人,当他们必须学习一门新的学科时,却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成问题。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做。我们大体上很有信心,假如你想严肃地研究一门学问,你是知道学习这门学问的技能的”(Hayek 1983b,30)。只要研究一下哈耶克的著作,就会知道此言不虚。
哈耶克在大学最初的一年半钻研心理学。1919年至1920年冬天他的苏黎士之行显然十分重要。那一年维也纳的冬天十分可怕:城里很多人冻馁难耐,天气冷得不行,缺少燃料使大学不得不关门。哈耶克的家人安排了这次旅行,既是为了让他脱离这种凄凉的环境,也是为了在他的疟疾痊愈后帮他恢复健康。在苏黎士时,他去听了有关教会法和石里克思想的课(没过几年,莫里兹·石里克就继阿道夫·斯托尔接任了恩斯特·马赫的教席,不久便开办了自己的讨论班,它很快以“维也纳小组”著称于世)。在瑞士期间,哈耶克还在大脑解剖学家康斯坦丁·莫纳克夫的实验室里工作了几周,对大脑纤维束进行分析。1920年他开始撰写一篇论文(题为
“beitrfige zur Theorie der。Entwicklung des Rewusst—seins”,英译本见}]ayek[1920]1991a),此文既受到恩斯特·马-赫思想的启发,又想对他发起挑战(参见IIayek 1994,63—64)。
哈耶克后来说(}Iayek 1992d,172—73),由于种种原因,马赫有着理所当然的吸引力。他的实证主义著作甚至在战前就影响着社会科学,这有熊彼特受到它们的吸引为证。在战后时期,维也纳大学的一些教授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学科,石里克一出现,实证主义便和维也纳大学有了不解之缘。马赫哲学在政界的左派中很走红,但它甚至也为中间派提供了科学依据,用来对抗最恶劣最放肆的形而上学,当时流行的许多社会研究方法(譬如奥斯玛尔·斯潘的“直觉普遍主义”[intuitive universalism]。我下面还会谈到他)都受到它的影响。
哈耶克在回忆往事时说,他本人的兴趣被激发起来,是因为“对马赫的现象主义的怀疑,在这种现象主义中,纯粹而简单的感觉是所有感性认知的要素”:“马赫的感觉心理学中的‘简单而纯粹的感觉’这个概念几乎毫无意义。马赫把很多感觉之间的关联定性为‘关系’,使我最后只能断定,感觉世界的整个结构来自于c关系’,因此可以完全抛弃纯粹而简单的感觉这个概念,而它在马赫的思想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1992d,174)。哈耶克把马赫诉诸感觉的做法称为毫无意义(大概有嘲弄的意味),是在用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去批评马赫的感觉理论。哈耶克的论证是,既然马赫坚持消除多余的理论对象,最简单的理论才是最好的理论,因此他的感觉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心理学家阿道夫·斯托尔读了哈耶克的文章并给予鼓励,德国哲学家阿洛伊斯·利耶尔也是如此~一哈耶克也给他寄去了文章的副本。不过,哈耶克在1920年9月为了准备法学考试,把这篇文章放在了一边。它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一躺就是25年。哈耶克在1945年又回到了这个题目,它终于变成了他的理论心理学著作《感觉的秩序》(}tayek[1952]1967h)的基础。就像1920年代一样,他在《感觉的秩序》中采用的论证方式,是要证明一种特定的科学立场(在这里是指行为主义)为何会与给它提供所谓基础的哲学立场不一致。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考察这部著作。
既然哈耶克对心理学感兴趣,他为何最终又决定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他徘徊于两者之间,但在维也纳大学它们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两位主要的心理学教授都死于战争。仅存的斯托尔教授虽然仍在教课,但也死期将至。至于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和边际主义德语教科书的伟大作者欧根·菲利波维奇。冯。菲里普斯伯格,1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们的继任者是卡尔·格伦伯格和奥斯玛尔·斯潘,前者是个经济史专家和社会主义者,后来协助建立了法兰克福学派。
斯潘在1919年获得教席,他相对年轻,活力十足,讲课十分生动感人,是个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斯潘在1920年夏季学年开设了论‘理想国家’(Der wahre Staat)的讲座,旋即爆得大名。斯潘的名气在学生们中间迅速传播,他们蜂拥而至,到课堂里听他讲课,为他痛斥老一代人那些不中用的理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一拍手叫好。他描绘了一幅新社会的蓝图,在这个社会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Craver‘1986,9)。斯潘是直觉普遍主义的先知。按这种学说,知识是通过对各种社会学整体的本质特征的直觉想象而获得的。只有这些本质是持久而真实的。不幸的是,它们是无法观察的,只能用直觉去认识它们。具备这种直觉能力的专家,也就是应当制定政策的人,因为他们的政策是有益于整体的政策。斯潘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类的信条,因为它们对一种至关重要的真知灼见构成了干扰:所有的价值必须从它对集体的意义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虽然斯潘反对反犹主义,德奥合并之后甚至被禁止教学,并坐了5个月的牢,但他的学说却为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依据,因为他的观点能给所有的威权主义政策提供正当性(Schweinzer。2000)。他的理论今天听起来像是奇谈怪论,这个事实大概只能进一步证明科学的世界观受到了怎样的围攻。斯潘的体系是货真价实的“胡说八道”,它使哈耶克这类有科学头脑的年轻人对马赫更感兴趣。
斯潘的名气只是昙花一现,许多学生很快就把他当成了笑料。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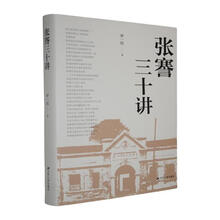
哈耶克是一个谜。距今20多年以前,他在我眼里就是这样。
那是1982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大学一个学年的博士后就要结束。几年以前,我作为一名助教,以一项经济思想史的专业研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论文有个一本正经的学究式题目:“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经济学方法论”。我去纽约大学的部分原因是,我想把它改写成一本人们确实愿意读的书,此外,我还想在那儿研究一下奥地利人的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进一步了解奥地利人独特的方法论观点。它们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实证主义话语大不相同,实际上是跟这种话语针锋相对的。我尤其想进一步了解米瑟斯所提倡的那种怪怪的。先验主义方法论,至于哈耶克,我对他几乎还一无所知。
如果您想了解奥地利人的运动,纽约大学是个好去处。那儿有(至今仍有)为研究奥地利经济学而设的正式课程。除了课程之外,还有每周的讨论课、教职基金、博士后和研究生。我在那儿的一年里,教师有伊斯莱尔·基尔泽纳尔、马里奥·里佐、杰里·奥德里斯考和路德维希·拉赫曼(春季学期)。拉里·怀特任客座教授,理查·朗格卢瓦是博士后,还有十几名学生,其中包括唐·波德鲁、马克·布莱迪、桑迪·伊科达、罗杰·科普尔、库特·舒勒和乔治·塞尔金。这里人才荟萃,对我而言是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
那年春天,杰里·奥德里斯考递给我一本特伦斯·哈奇森的书,然后问我:“哈奇森认为哈耶克有过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你怎么看?”哈奇森曾说,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次“方法论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更确切地说,他认为哈耶克在1937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标志着哈耶克已脱离了米瑟斯的先验主义立场,转向哲学家卡尔·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方法论(Hutchison 1981,chap.7;另见Hayek [1937]1948a)。
我对这种说法颇为不解。我在做博士论文时深入研究过波普的思想,当时对米瑟斯的观点也有较多的了解。坦率地说,难以想像还有比他们两人更加南辕北辙的两种观点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呢?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哈耶克是他们两人的好友。哈奇森是数一数二的思想史专家,而且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提供了详尽的文本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因此,哈奇森的说法带来了一个谜。正是为了解开这个谜,我开始专攻哈耶克。从此以后便潜心于此,尽管有些关心我的朋友也曾好言相劝,别把自己那么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希望在这篇导言里解释一下自己矢志于此的若干原因。
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学术生涯的最初八九年里是用德语写作。后来,至少直到1962年去德国以前,他主要是用英语写作。也许是采用新的语言表达思想的新鲜感和挑战,他在选择标题上十分用心,有时用它们来暗示另一些著作。譬如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说“经济思想的趋势”便暗示着《经济学的趋势》,一本由雷克斯福德·图格维尔编辑、十年前在美国出版的著作(见Hayek[1933]1991c;Tugwell[1924]1930)。他的知名度最高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1976b),标题是取自托克维尔的一句话“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vitude)”(见Hayek 1983b,76)。另外,我估计,他在芬莱讲座上的讲稿“个人主义:真与假”[1946]1948c),也是在暗指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这篇文章中一段有关个人主义的话。
有时标题还包含着多层含义。使哈奇森认为哈耶克有个“方法论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那篇文章,即“经济学与知识”,便是其中之一。它的主题是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有关实践者的知识的假说,但也涉及经济学家本人能够知道什么。对哈耶克的诺贝尔奖演说“知识的僭妄”([1975]1978a)也可以做如是观。我本人的标题“哈耶克的挑战”便是遵循着哈耶克的引导,这个标题是指围绕他的著作出现的多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