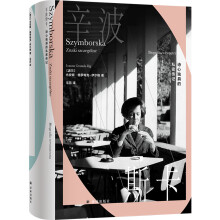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属狗,满族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现为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院内北房,时在阳历1899年2月3日黄昏,也就是阴历戊戌年(1898年)腊月二十三酉时。
依中国时岁民俗,这天是“小年”,灶王爷要去西天,上报人间“好事”,“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可谓生逢良辰节日,以至连一向脾性恶劣的姑母,都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呢!”
又因次日恰“立春”,是一年中的头一个节气,乃取名“庆春”。
“可以想象得到,当初我的父母必是这么看:有子名春,来头必大,定会光宗耀祖。还可以想象得到:春字这个吉祥字,父母当然希望儿女美似春花,一生吉利,万事亨通。”
“舍予”则是“舒”字的分拆。而笔名“老舍”,与他的姓、字相关,都含了一个“舍”在内。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见于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号上。
老舍的出身和名号如此考究“传奇”,我们若单自这一点说,他的一生,“春”确是“庆”到了,“来历”也被自己作出的斐然成就证实,世称他是“五四”一代现代作家甚至整个20世纪作家中,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和“著名大师”和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但一生终结,却也在那个“舍”里藏了——一生信仰所系在“牺牲自我”,可“老”是“舍”“予”着,最后连性命都“舍”却不要,而投了太平湖。
这是后话。
即使被姑母言中,老舍确不是凡人,可在起步阶段,凄苦沾染了生活的全部。这种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后来以“月牙儿”这个物象,来透露童小心迹:那是“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照着我的泪”。
这个感受很重要,几乎决定了他一生命笔的主要取向和底调。正是有了一个惨淡酸涩的童年,最终造就了老舍那颗刚强而伟大的平民作家的魂灵。
老舍出生前,他父母已生过三位哥哥、四位姐姐,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却只有四人:大姐、二姐、三姐、三哥。
他是母亲的“老儿子”,生他时,母亲41岁,两个姐姐出嫁,三姐十一二岁,哥哥八九岁,姑母守寡,和他们一起生活。
算来一家六七口,进项只有父亲舒永寿每月的三两银子。
舒永寿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属满族“八旗”里的“正红旗”。除了春秋两季尚能发一点米,接补生计,再无别的生活来源。因此,家中苦时每天只吃两顿饭,把一点菜叶子和粮食,掺进酸豆汁汤,熬成稀糊糊喝。
也许身体太弱的缘故,老舍一生下,就给家庭带来不幸:父亲不在家,城里正当值,滴水成冰,接生婆缺经验,母亲又营养不良,生养时失血过多,晕了过去,半夜才醒来。幸亏他大姐从婆家及时赶回来,揣他人怀,才保住老舍一条命。
到他一岁多时,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
“皇上跑了……满城是血光”,“处处是火舌,火柱,飞舞,吐动,摇摆,颠狂。忽然哗啦一声,一架房倒下去,火星,焦碳,尘土,白烟,一齐飞扬,火苗压在下面,一齐在底下往横里吐射,象千百条探头吐舌的火蛇。静寂,静寂,火蛇慢慢的,忍耐的,往上翻。绕到上边来,与高处的火结到一处,通明,纯亮,忽忽的响着”。
城里的守兵,为着民族气节,更为着一个腐朽不堪的王朝,拼死抵御敌寇。
舒永寿也在正阳门阻击,用的是老式抬枪,需要随放随装火药。
不幸,敌人的子弹打着他身边的火药,同时把他身上的火药燃着,他遍体烧伤,爬进南长街一家粮店,即现在的西华门副食商店。
里面没有人,全跑了。他就一直躺在那里。
后来还是他内侄败下阵来,闯进去找水喝,才发现了他。见他浑身都烧肿,已不能说话,只颤抖着将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和裤腿带交给内侄。
内侄想把垂死的姑父背回家,可外面正乱,慌忙逃出去,急急去报信,进门就“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