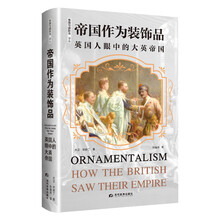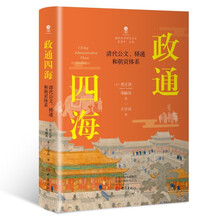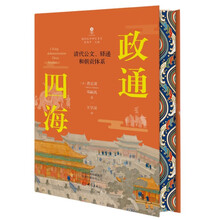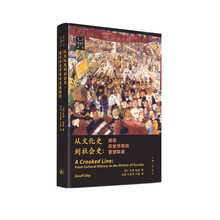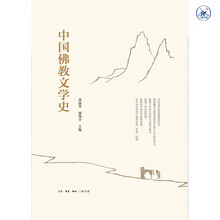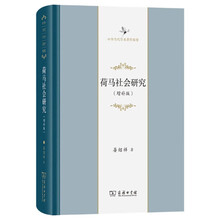当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如同闪电般划过历史的天空时,有关方面考虑的是要进行认真的科学认定和认证,那就是从日寇侵略中国时期他们所制定的“慰安妇制度”方面对周大娘的身份做出科学的最终的认证。
这是对历史负责的重要论证。
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男性对女性集体奴役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见苏智良先生《慰安妇研究》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
周粉英大娘的正义宣布,首先感动了孙宅巍教授。5月9日下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教授立刻赶往周粉英大娘家中,他的任务是对周大娘“慰安妇”的经历进行调查与核实。
孙教授的调查是按着国际惯例的考察论证方法来进行的。他将从三个方面对周粉英大娘到底是不是“慰安妇”进行认定。
这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在不久前,日本一小撮右翼分子以不曾在中国设立慰安所机构为由,否认曾在中国实行过慰安妇制度。所以,周粉英大娘当年到底是慰安妇还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孙教授所施用的是使用学界关于“慰安妇”的定义条例进行核实。其中有这样三个定义:
一是固定时间。指受害者遭受较长时间的欺辱:
二是固定的地点。不止一个受害者被掳往固定的地点为日军“服务”:
三是固定的“服务对象”。受害者被逼专为日军“服务”。
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先生也随孙宅巍教授一同考察认证。他们来到周粉英老人家,先送上慰问金之后,吴先斌拿出他收藏的一枚日军当年遗留的避孕套,问老人当年是否也见过。一阵摸索之后,周粉英大娘肯定地表示,当年就是用这个,每次被欺辱时都要用。
得到答案之后,吴先斌向在场的记者和相关媒体介绍说:“周大娘的身份已被确认。日军当年对周奶奶的暴行毋庸置疑。”他同时指出,日军内部对其士兵到慰安所发泄兽欲有详细的规定,其中一项就是必须要使用避孕套。如有人不用,被发现后会遭到相当严厉的处罚,这是慰安所区别于一般妓院的一点。
吴先斌作出的最后结论完全符合历史上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科学论证,这些问题在《慰安妇研究》中有大量的记述。如当年曾参加过日本侵华战争,晚年写出了诸多当年在中国的战事记载的日本士兵东史郎,就在他的战地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去慰安所糟蹋妇女的场景:
昭和十三年(1938)一月某日,南京街面被占领一个月后。电灯亮了,雨夹着雪下起来。“联络!有愿去慰安所的报名!”传来了通知。据说几天前,5台卡车拉着日本来的卖春妇在街上展览似的逛了一圈儿,在士兵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喂,中山路拐角的空房子里有10个女人!”
“这间洋房里有30人呢,有中国妞还有朝鲜妞!”士兵们像过节的孩子似的喧闹着。
我们分队去了一个后备兵叫金桥的。以前发给士兵用的是朝鲜银行支票,这次为了“买女人”,第一次给了军票。一等兵金桥拿着发给的军票和避孕套,顶着寒风兴冲冲地去了。晚上他嘻嘻笑着回来了。把床上的毛毯裹在身上,打开了日记本,像要作重大纪念似的,描绘着刚才那女人的房子,斜着的楼梯下有一张床,连姑娘的牌号都记上了,还有花姑娘上床的姿态,感觉真好。只是入口处站着宪兵。按顺序排队的士兵也吵吵嚷嚷的,这样的话,就没有时间全脱光了,没法慢慢干,不过也还是蛮棒的。从外面可以清楚看见各房间的全貌,只是谁也不在意,各干各的。他边说着边用笔记在本子上。
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各种资料表明,他们制定的诸多《慰安所规定》、《军人俱乐部规定》、《有关外出及军人俱乐部规定》等条款中都明确规定,慰安场所的“利用者限于军人和军队聘用人员”,为了防止性病必须使用避孕套。在日本人吉见义明编著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见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229页)中记载,“在有条件的慰安所,日军派出值日官,监督日军士兵使用避孕套。如查出不使用者,就取消其进入慰安所的资格……”
在孙宅巍和吴先斌先生详细询问了周粉英老人当时被掳情况之后,又在周粉英儿子姜伟勋带领下来到了白蒲镇曾给周粉英老人带来无尽屈辱和痛苦的慰安所旧址考察。当这一切都进行完之后,孙教授面色凝重地告诉《扬子晚报》的随同记者说,周粉英大娘是一个典型的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这个铁证已不容否认。同时,他对老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无比的钦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