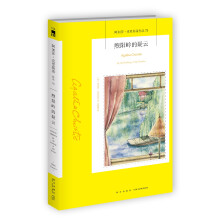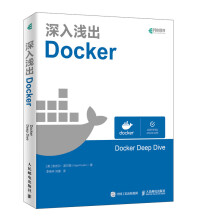引论
三晋文化是山西文化的源头吗?
兼论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
先秦是我国地区性政权最多,地域色彩最浓烈的时期,特别是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后,跨入战国时代的七国均背依一定的经济区与风俗区,并峙称雄,那个时代区域文化的某些特质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不同区域历史前进的方向和步伐”[1]。所以,人们常以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等代指各地区文化。这一说法影响广泛,诸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5年首批推出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12种,其中以战国国家名称冠名者超过一半。[2]对此,该书“编者札记”做如下解释:
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当然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学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迁移,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显然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
编入该丛书的《三晋文化》是关于古代山西文化的撷取式叙述。对于三晋文化与山西文化的关系,作者说:“由于唐国始封时的国都唐,改称晋国后历迁之国都冀、曲沃、绛、新田,都在山西地区,三晋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它们所辖的区域,只有山西省是全部据有,因此后世也就用‘晋’、‘三晋’来代指山西地区、山西省。本书取名为‘三晋文化’,也是由此而来。”[3]在这里,“三晋文化”相对于“山西文化”,仅是地名雅称的沿袭。
山西学者李元庆先生最早针对晋及三晋文化提出“国家文化”的概念。他对以往“如同人们习惯于以‘晋’或‘三晋’来简称山西省一样,举凡山西地区的传统文化,往往冠之以‘晋文化’或‘三晋文化’的称谓”的含糊界定表示质疑,提出“基于概念的严密性和准确性……”,‘晋文化’概念乃是对西周至春秋时代晋国文化的确指,‘三晋文化’则是对于战国时代魏、韩、赵三国国家文化的确指”。将“晋文化”与“三晋文化”统称为“三晋古文化”,并认为晋国立国前的山西地区远古文化为它的历史渊源,之后则均属于三晋古文化的遗风余韵及历史流变,同时得出“三晋古文化是山西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或者说是成熟形态”的结论。[1]
另外,以山西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为主体编撰出版的多卷本《山西通史》,对“山西文化”有如下明确定义:“山西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逐渐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化特征,这就是三晋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是以华夏文化以及晋文化为核心,容纳边塞游牧文化以及佛教为代表的印度、希腊文化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化系统。”[2]至此,山西地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晋文化(包括晋与三晋)是山西古代文化的本体或核心。
“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概念的相继提出,无疑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先秦特殊的国家文化与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的关系。但是细究三晋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特质,却发现山西学者的判定显然忽视了三晋文化产生的特殊政治地理背景,没有注意到“国家文化”与“地域文化”结合及背离的关系问题。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国家的解释为:国家可以指一种历史实体或一种哲学思想。国家要求共同体与领土之间有一种固定的联系。同时此类政治共同体有一些超越时空的一般特性。[3]可以看出这一概念本身包括着着地与离地两重性。把国家作为一个运动中的政治实体,它既拥有政区(等级、幅员)、边界、首都等对文化有硬性规范的实土内容,还承载着对学术与民风具有指导性的政治思潮和政治习俗,后者由于常常随政治格局的组合变化而迅速改变,有可能成为一种虚土现象。在中国最典型的这种表现恰恰是战国的韩、赵、魏文化。
三家分晋以及随后各自的争城扩地后,韩、赵、魏的疆域主体部分均由两大块地理单元组成:魏有山西河东之地和河南北、东部;韩占山西上党地区和河南伊、洛、河三川之地;赵据山西中北部和河北西、南部。在这期间,三家都经历了国都数迁的过程。大致说来,魏从安邑徙大梁,韩从平阳迁新郑,赵从晋阳到邯郸,其指向均由相对封闭的山西高原向开阔的中原平川移进,这标志着三晋的发展重点都先后离开了山西。因为两周之际,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还保持着名义上的最高权威,特别是在周室东迁中立了大功的秦、晋都深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个中微妙,所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狐偃就对晋侯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史记?晋世家》文公二年,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令尊王,晋之资也。”这次周室内乱中,由于先秦一步,纳襄王入成周,晋国得到了河内阳樊八邑的赏赐,大大地增强了它日后逐鹿中原的实力。后自晋而出的韩、赵、魏,无不遵循这一建国方针。当时人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1],这种有利的地理形势产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秦惠王时,为伐蜀或伐韩而犹豫不决,张仪主张伐韩,司马错反对说:“今攻韩而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2]惠王听了,遂西向伐蜀。昭王时,范雎至秦,说秦王曰:“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3]《史记?乐毅列传》记毅子乐闲劝燕王语,亦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伐之不可。”
“争于市朝”的政治策略,一方面使晋及据晋之大部的魏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强大的霸主地位,同时使三晋文化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和急功近利的色彩。严耕望通过对战国时期主要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籍贯和一生主要活动地点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三晋主要有名、法、纵横三家,除名家外,大抵即以三晋为局限,分布于大河中游(三门峡以下)之南北,河淮平原中北部,所谓大河南北,纵横范围不逾三百公里。特别是法家名师之地理分布极为集中,其籍居,南北直线距离不过约二百五十公里,东西距离更狭,仅约一百二十公里,他称其为“三晋核心地带”。[4]而这恰恰是韩、赵、魏在山西之外的主体部分,当时的“天下之市朝”。至于名、法、纵横三家的学术思想,名家的出现是有感于春秋战国之世名实乖乱而有了正名的要求,其发展本质走入哲学一途,与现实并无直接关系,为儒、墨、道、法诸家的基础,而“持是术也,用诸政治,以综核名实,则为法家之学”。[5]吕思勉先生曾说:“切于东周事势者,实为法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则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纵横家,更是当日政治权术的实施者。
《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法家的实践者,纵横家的游说对象皆秦人。秦晋文化的这种递承关系,更有力地说明秦晋当日政治地理位置的差异。秦人的祖先早期在西边为周王室养马,“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狄遇之”,后来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但是仍然被目为西戎,摒弃于中原文化之外。秦孝公时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发愤图强。但是秦昭王四十多年时,中原对它的评价仍然是“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所以它几乎是既无宗法贵族之习惯,又无宗法礼义之观念,这就决定日后它能最快适应时代变革。晋国虽然长期与戎狄混处,骊姬之乱,又尽逐群公子,自是无公族,大大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但是它身为姬姓之国,作为周室的宗亲,身份自与秦国大不相同。比如在对待戎狄的态度上,戎人因“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1],归顺晋国;而晋国“魏绛和戎,戎狄朝晋”,是以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来安抚四夷,以后晋及三晋屡屡打出“尊王攘夷”的招牌,维护其政治上的优势。处于政治权力斗争的的漩涡,虽然能够产生最切于时势的政治思想,但是也容易丧失自己的特点。荀子入秦,应侯问他的观感,他虽然夸奖秦国治理有方,同时也指出,“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短也”。[2]荀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说他是“赵人”,虽未明指为赵地何处,但是从他一生行迹及学术思想兼及儒法,应该是赵国在山西境外漳河流域一带之人。他指责秦国缺少儒家教化,也正说明秦国政治思想的纯粹;以后他最得意的两个弟子李斯、韩非皆主张法家之说,助秦统一六国。荀子一门师承学术关系说明三晋虽然可以产生最新的思想,却也因此不能守而致之,最终实践其学说的还是“拥一关而俯天下”的秦人,所以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将东周列国时代划分为七大文化圈,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即黄河中游划为中原文化圈,秦文化则是独立的[3],这是相当有见识的。
另外在三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件事是“子夏居西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礼记》云:河东故号龙门河为西河,汉因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处。《正义》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后世认为这件事对当时魏国的发展和相当长时间内当地文化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汉书?儒林传》曰:“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嫠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西汉时杨恽失势,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劝他应闭门思过,他就以这件事反唇相讥,说:“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慨,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风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1]而后更有“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群俊兢立,名过齐桓,秦人不敢规兵于西河”的议论。[2]事实上,先秦文献中“西河”并非一地,虽然今山西境内一段因秦汉西河郡的设置特为彰著,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第38条却已辨明“子夏居西河在东方河济之间不在西土龙门汾州”,即东方相州之安阳,黄河以西,今长垣之北,观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带之河滨,魏文侯当日居于邺城。[3]此说无可辩驳,则子夏居西河,仍在三晋核心地带,于今天山西地区无涉。黄河中游以西,龙门之附近,其地在战国初尚无文教可言。
战国时代,社会性质发生急剧变化,传统宗法制度受到了强烈冲击,所谓“周礼弃地”,社会风俗相应转变。《史记?平准书》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刘向《战国策?书录》总结战国的特点,“贱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处于政治冲突中心的三晋则直接体现了这一政俗。《战国策》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像“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像“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以及“韩氏辅国也,好利而恶难,好利,可营也,恶难,可惧也”等等。[4]三晋核心区域的民风也是惊人的一致。据《汉书?地理志》九州风俗记载:
(河内)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秦既灭韩,徙天不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藏匿难制御也。
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先。 (赵、中山)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 (邯郸)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卫地)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
虽然对于三晋各地风俗的强烈传承性,《汉志》风俗篇的作者朱赣都试图一一从历史上追溯源起,事实上,这是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的共性及法家“严而少恩”的特点相一致的,为二百六十年社会风气的主流遗存。否则,如果不是曾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仅仅依靠个别人的力量和影响,是很难使同一的风俗在政治文化背景已经改变这么久后大面积留存。今山西省境内与三晋核心地带习俗相近的只有太原、上党一线。《汉志》说:“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太原的特殊性无须赘言。同样,在“争于市朝”的政治策略下,上党成为山西腹里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交通直道,韩、赵、魏在此争夺激烈(上党交通孔道的形成,容后论述);及全国统一日久,《隋书?地理志》就说:“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性尤质朴,盖少轻诈”,与《汉志》所载已有天壤之别。而晋国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河东在自己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上生成的习俗和韩、赵、魏的共性绝不相类。《汉志》说:“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国风》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这和山西长期陋实、俭啬的民风是一致的。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韩、赵、魏文化中相当有特色的两点与山西的文化性格完全无关。其一,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为倡优……女子弹弦踮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其二,与韩、魏亲邻又先后被侵夺的郑“土隇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俗称郑卫之音”。卢云说:“赵、中山的核心部分太行山东麓地带……具有良好的交通地理条件,这一狭长地带,很早就兴起一系列都市城邑,其间形成了先秦汉晋时期最重要的南北商道,所以在赵、中山一带,女子接触行商富贾的机会较多,眼界较为开阔,在商业发达的环境里,也易于形成攀比富贵的社会心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女子远出周游,奔嫁权势的风气,致使奔婚的残余形式长期保留。”[1]对于后者,他认为这是古代族外群婚在过渡阶段转化为“男女聚会”这一形式,为先秦时期华夏族的普遍习俗,而“郑卫人在对待性关系上比其他地区的居民更为随便”。时代的变化往往首先体现于女性文化。赵女郑姬的“游媚富贵”无疑是城市文化的代表。郑卫之音则成为当时的流行音乐,魏文侯最好古,却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如果说这是两种落后婚姻形态的残留,那么落后的形态何以在经济发达区转为时尚,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当时的环境中获得新的动力,《盐铁论?毁学》说得好,“赵女不择媿好,郑妪不择远近……皆为利禄也”,这仍然是战国的时代特性。
综上所述,晋国由于长期与戎狄相处,虽为周室宗亲,不像齐、鲁、郑、宋受儒家礼教熏染之深,在争霸兴国的过程中,通过小宗代兴,尽灭公族,作爰田、作州兵、铸刑鼎等一系列活动,不断摆脱旧的束缚,增添新的活力,终于跻身于大国之列。同时身为姬姓之国,他又要在周王室威望衰退后,实现领导中原诸夏王国的雄图霸业,这样在“争于市朝”的政治策略下,三分晋地的韩、赵、魏的发展重点先后离开山西,进入周室所在的中原地区;同时也使三晋文化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和急功近利的色彩,于学术,法家、纵横家最切于时势,于民风,好利恶难,苟以取强乃战国之共性。所以不能说山西和三晋核心地带的文化毫无关系,至少有相当的差异。
三晋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处于政治冲突中心的国家所承载的文化往往直接体现时代的风貌,而与该国所据有的实土形成相当的“离地度”,如果把把三晋文化视为山西文化的直接源头甚至是山西古代文化的成熟形态,无异于忽视了山西文化在漫长历史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地域差异和自身特质。这是本书接下来要讨论的主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