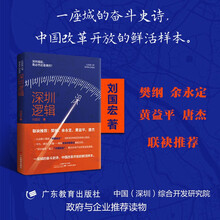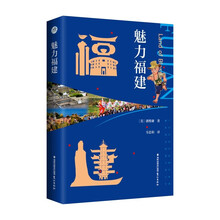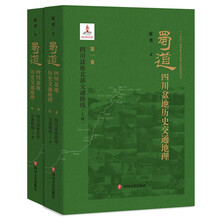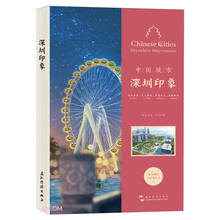三岁孩童看到的“七七事变”<br> 1937年6月23日(阴历五月十五),我三周岁。作为西琉璃厂一个家道殷实的书商——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北平分局经理胡柏桢的独子,这个生日过得体面热闹。重要的是自此我有了明确的记忆,包括此前幼小还没记事时,母亲事后对我讲的事,我也大多留在了脑海中,至今难忘。生我时,上面已有三女,才见男孩,故大办喜三、弥月,之后父亲四十大寿又大办,甚而还在家中请了杂耍“堂会”。大概由于过于张扬而引发恶人的觊觎:接到恐吓信,让把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埋在虎坊桥京华印书馆大楼西后墙有白圈处的土中,“否则要你小儿子的命!”去看,墙上果有白圈,立即报警。警方蹲守几日,匪未获,又在父母床头安了直通巡警阁的警铃。(这我倒见过,常因误碰警铃电线而警察赶来,虚惊一场,后慢慢塌实了,警铃就拆了。)给我雇了奶妈,两周岁断奶后奶妈离去,我哭闹几天几夜找她,任何人不跟。(后,我大点了,奶妈曾回来看过我,记得她是个不高也不胖、很利落的小脚妇人,我已不那么离不开她了。)我得麻疹憋住出不来,幸得儿科名医周慕新几副中药,救了命……<br> 进了7月,我提前一岁考上了十分难考、十中取一的师大一附小幼稚园,母亲高兴,邻居朋友夸,可父亲脸色却有些阴沉,“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来”常挂在大人嘴边。此前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抡大刀片砍日本鬼子,则是大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资,我也听见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天,父亲突然领着我出门往西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这是一座建于1922年(楼顶有镌字)带地下室的四层西式楼房,今仍存,是新书业从上海进军北京琉璃厂的领军者。父亲带着我进去,没让我去看五光十色的店堂,而是直奔楼顶平台。平台上已有几位书业的叔叔伯伯,都极目往南远眺。北京是北高南低,那时南城几乎没有高楼,只琉璃厂的商务、虎坊桥的京华大楼(今亦存,这是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投资兴建的,是为新书业进军北京的前奏)和万明路的新世界(是个五层楼的游艺场,仿上海大世界;今已翻盖成高层酒店)三座,其他多是低矮平房,又没有空气污染,能看出老远。只见南边上空有不少白亮点飞上飞下,不时从下面窜上几朵白云似的东西散开在亮点周围,之后传来隆隆炮声。这是日本飞机在轰炸南苑机场,我军高射炮还击乏力,赵登禹将军就牺牲于是役。大人们摇头叹气:“恐怕二十九军顶不住,这回日本人真要来了。”<br> 这些当时我不明白,还是照玩我的。家里突然要施工:在北厢房修个地窖子。一动工,最高兴的是孩子,多有意思呀。地窨子有一间房大小,掀起屋内漫地的方砖直挖下去,墙四周和地面抹水泥,顶子架上厚木板,再原样漫地面砖,留有加木盖的入口,下有木梯,在院子的窗台墙下还留有加铁篦子的通气孔,是个防空袭的家庭防空洞,几天就完工了。没等修好,我们姐弟就找机会爬上爬下,真带劲。领工的是我二师兄贺家亨的大哥贺家麟,对我们的淘气和干扰,也不好说什么。地窖子里运下去几包澳洲金豹面和仰光米,还装了电灯,就是没人想到挨炸后没水没火没电,即使有米面又怎么弄熟了吃?何况地窨子里非常潮湿,一下雨气孔还进水,米面都长了毛,一天也没用过。只有一样好处:天热时掀开地窖子木盖,从下面往上冒凉气,等于天然空调。几年后怕塌,就把地窨子给填了。<br> 天热,外婆下午常带我到南新华街“豆汁张”摊前的大槐树下玩,玩伴是一得阁墨汁厂的少老板、后师大一附小同学徐新民。那天正玩得高兴,我的三师兄王振铎突然跑来,抱起我,扶着外婆:“姥姥,快回家,日本兵进城了!”只见琉璃厂各铺眼都乒乒乓乓上板关门,转瞬间路静人稀、鸦雀无声。只听得大街上呱、呱的皮靴声,师兄们把上了板的门轻轻推开一条缝,悄悄往东看,我也挤着钻出脑袋瞧,见大队日本兵正在南新华街上往北行进。从这天起,北平这座古城完全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据一位当时在北平、现居美国的父执辈说:这天是7月29日,日本兵从广安门进城;也有说是8月初的。我没查。<br> 还有个小插曲:9月1日开学,我上了幼稚园。记不清是同年还是第二年,一天F午,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噼啦啪啦声音响个不停,像打枪。学校里、街面上全乱了,家近的赶紧接孩子回家,店铺又忙着上板,全以为日本人要屠城!谁知是东琉璃厂以卖花盒子出名的九隆斋花炮店着火,鞭炮一炸,很像打枪开炮,又是虚惊。70年后,当年老同学见面忆旧说古,九隆斋着火把大家吓得够戗必会提到,心中难免泛起亡国奴的酸味。后来据我的中学数学老师、也是师大附中、一附小的大学长钟善基先生说,九隆斋着大火是1938年,不是1937年,那时他正在师大附中上高中。<br> 北平沦陷后,先父曾说过:“等咱们军队打回来,到九隆斋(着火后又修复重张)买它几千响大钢鞭放放,出一出亡国奴的晦气!”父亲是从不放鞭炮的,这也影响到后来的我;而他这点爱国的拳拳之心,深深地镌入我童年的脑海中,永难相忘。<br> 和平门看火车不敢再去<br> 和平门是民国后才修的,不在老北京的内城九门之内。今仅具名,城早已失存。据云:早在北洋名宦朱启钤主政时,为疏通内外城交通,先在正阳门东西各开城洞,又计划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中间开一城门,打通从虎坊桥到长安街的交通大道,以免从南城进城的绕道之苦。但此双城洞的和平门直到北伐成功后才开通,又在护城河上建了一座很平宽的石桥,南北成通途。科学大师钱学森1981年在他的母校师大附中80年校庆大会上说:他20年代中期考进师大附中,那时家住内城,每天上学要绕路出宣武门走西河沿到校,因为还没有和平门;1929年入师大附中的京剧大艺术家赵荣琛,已能从绒线胡同住家出和平门上学,近了不少。<br> 有和平门之前,贴着城墙就有了铁路,介于城墙和护城河之间,是京汉线,客货车都走,火车站在前门箭楼西,俗称西车站;箭楼东侧还有个火车站(今仍存,称“老车站”),走京山、京沪线客车,俗称东车站。我记事时就是这样。尤其和平门(包括其他城墙外有铁路的城门)老过火车,一过火车就要拦住车马行人,先是铁路两侧有轱辘能推动的铁栅栏,后来换成现在郊区路口仍使用的扬起下落的拦路杆,火车过去再放行。<br> 去和平门看火车是我幼年时最大的乐趣之一。下午睡醒午觉,外婆推着藤编的双座小孩车(俗称“婆婆车”,后来改藤为竹,现已绝迹),我坐在一边,另一边放着个小板凳,就去看火车了。到了铁路旁,找个河边树荫处,我又玩又看,外婆坐在带来的小板凳上看着我,天热时扇着大芭蕉扇。来来往往的火车,有绿色的开往平汉线的客车,有拉煤的货车,巨大的火车头,转动的“长臂”,响亮的汽笛声,刚过去,又挂上几辆空车倒回来,真有劲,一去就不想回家。那时护城河若不下雨,水也不多,虽有下水道通向河中,污染不厉害。外婆只管看我,没别的事,家里另有做饭干家务的老妈子,天快黑才推我回家。<br> 看火车看迷了,在家中找几个木板凳,倒过来用麻绳连在一起,模仿着火车,我嘴里学着火车的各种声响,拉着这列“板凳火车”在院子里绕圈,自得其乐。<br> “七七事变”后日本兵一进城,和平门的城门半关(不止于此,那时一有点什么事,北京头一件事就是关城门,全关或只关一扇),有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凶神恶煞地站岗,过往行人不许停留,也不敢停留,当然也包括我们祖孙这铁道边上看火车玩的。这是我上幼稚园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正惦记出去玩呢,老是窝在“豆汁张”摊前的大槐树底下,长了,没劲。上哪玩去呀?!<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