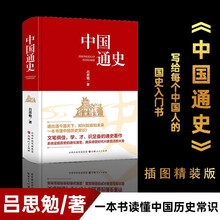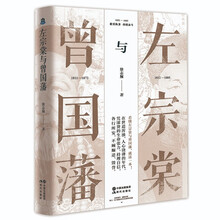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换而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 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iville)所说: 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不可能的。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 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国会何以能救亡?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 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梁启超只是理论家。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谘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导发。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见诸实行。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法国人见美国革命的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结论
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换而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 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iville)所说: 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不可能的。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 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国会何以能救亡?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 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梁启超只是理论家。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谘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导发。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见诸实行。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法国人见美国革命的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