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 ,她写出了20世纪最好的历史作品。以《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从1956年到1988年,她共出版了10部作品:
《圣经与剑》(Bible and Sword, 1956)、《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 1958)、《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 1962)、《骄傲的城堡》(The Proud Tower, 1966)、《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71)、《来自中国的函件》(Notes from China, 1972)、《遥远的镜子》(A Distant Mirror, 1978)、《实践历史》(Practicing History, 1981)、《“荒唐”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 1984)、《第一次敬礼》(The First Salute, 1988)。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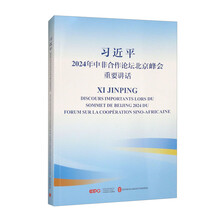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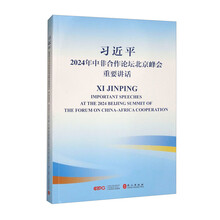




来源 价值中国网 郑伟强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它有关中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故事,中国仅仅是故事的特定背景,芭芭拉·塔奇曼以此获普利策奖就是一个证明——该奖只授予美国史的著作。读完全书,人们很容易获得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天真而典型的美国大兵在古怪的东方充满挫折和苦闷的漫长经历,不幸的是他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泥潭里。
在史迪威身上,再典型不过地集中了美国在二战东亚战场上的困境,无论性格、战争指挥权、策略重心和方向……盟友之间都争吵不断。今天外资进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都会遇到头疼的文化冲突与艰难磨合,数十年前在那样的非常时刻,其激烈程度自然更是十倍过之。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常言辞尖刻的“酸醋乔”还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事态的热切观察者,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甚至能用汉语向士兵训话。他对中国平民始终抱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理解,1929年还在一次演讲中含蓄地批评西方人动不动就说中国人“不可捉摸”,而他们仅仅是“跟我们不同”而已。在1941年太平洋事变爆发之前,他被公认为“对中国和远东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也就不奇怪了。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的紧急关头,毫无疑问会被罗斯福总统确信是派驻中国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不二人选,更何况罗斯福非常信任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史迪威极为推崇。
他的中国使命搞砸了
然而他却搞砸了。从任何意义上说,史迪威的中国使命都不能说是成功的。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一再恶化到完全无法共事,在缅甸热带雨林中的战争则是一次充满失败感的折磨,他的呼吁也很少人认真倾听——包括本国,因为美国当时将重心完全放在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则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出动陆军。将遭受珍珠港偷袭视为奇耻大辱的美国人,当时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对日本有私仇要报,在解决时不要别人插手。不过为避免难以承受的伤亡,对日作战主要由海空军承担,陆军方面只需要中国人帮忙尽力地拖住日本人。
史迪威多次不满地注意到,他负责的战区重要性极低,尤其是缅甸,最初根本就没预料到它会成为一个战区。不管他怎么呼吁,蒋介石经常无动于衷,而华盛顿也从来没有以实际行动响应他关于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建议。他饱受挫折,愤懑不平,仿佛一个手脚都被绑住的巨人,一身力气却使不开来,以至于那段时间里他本已够坏的脾气更加暴烈,此刻多骂几句至少也可聊以缓解他内心的郁闷。鉴于他前半生的和平年代里一直升迁极慢、仕途黯淡,1939年至1944年的五年里,却从上校连升四级至四星上将,无疑使他加倍珍惜这一迟迟到来的、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发挥才干的机遇,一心想做点什么。
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人,他耿直刚烈,是极鲜明的进攻型将领,他对战争的看法更接近于一场橄榄球比赛:要进攻、进攻、进攻。他发现中国人热衷于游击战,而他颇为讨厌这种躲躲闪闪的打法。他总是“时刻留意主动反攻的机会”,甚至“我愿意在一名下士带领下作战,只要他让我打仗”,他抱怨中国人的“头脑无法接受进攻的想法”。那么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怎么进攻呢?他的答复是“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优势”,以消耗取胜。
这种观念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都是痴人说梦。1941年底美国参战时中国已沦陷半壁江山,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消耗大半,而且国内根本没有统一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的美国观察家看来,“中国军队”仅是一种礼貌的称呼,因为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国家军队。在这种情形下,装备又极差,仅靠人多向日军发起正面进攻,那只意味着巨大的人员伤亡。1941年时最乐观的预估是1947年可以击败日本,要再拖六年,就必须“省着点花”,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内心都主张持久战、游击战,多拖一年是一年。他们对自己的那点家底太了解了。
“要改革这个体制,只能打碎它”
史迪威也许了解这些,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服从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中国把日本人拖住,以减少“我们的孩子”的伤亡。蒋介石的拖延战术,不到一年就让他受够了,他强烈地要求主动进攻,缅甸沦陷时就将最大的责任归咎于日军的“积极进攻”和“蒋介石的愚蠢、胆怯”。他这种“硬碰硬”橄榄球比赛式的进攻性思维无疑是典型美国式的,因此极了解美国人的宋美龄1943年初访美演讲时誓言中国人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就赢得全体议员掌声雷动。但私下里,她却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去,后来全部失去”。
在这个过程中,史迪威逐渐发展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战区的糜烂局势应完全由蒋介石来负责,他仅是一个“狗娘养的”自私专制的独裁者,只不过是“我们的狗娘养的”;蒋之所以不进攻,是因为他愚蠢胆怯,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势。他对蒋越失望,对抽象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就越有好感。由于他本人极力主张进攻,也就倾向于认为日军的获胜是因为主动进攻、而中国状况之差也因为消极防御。他对蒋接触越多,就越觉得,“要改革这个体制,只能打碎它”。最彻底的办法则是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
这听起来当然很有道理,例证也不胜枚举。最大的好处在于抚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实在无法忍受那么窝囊、郁闷、屈辱的“持久战”,宁可去光荣地冒险。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完全是匹夫之勇,小不忍则乱大谋。
20年后美国碰到的另一个泥潭
史迪威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去世。三年后的1949年,国民党军在大陆全面溃败。看起来他的预言完全实现了。当时的美国人在错愕之下,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古怪的结局,整整一代人都卷入这一反思:“谁失去了中国?”史迪威本人由此被视为一位受难而正确的先知,问题的答案似乎都蕴藏在他本人的经历之中。
1949年中国江山变色,对美国人的精神冲击之大,连中国人也很难想象。自晚清以来,美国以“门户开放”和传教热情逐渐介入中国政治,一战后欧洲列强势力退潮,日本则因为吃相太难看而替美国创造了将太平洋变为内湖的绝佳时机。在这一情形下,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成为美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斯福极力推动中国成为战后四大国之一(苏英对此均极冷淡);眼看一切顺利,不料历史却在此突然拐弯,出现的竟是一个红色中国!这怎么不叫美国人目瞪口呆呢?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就必须要有一个解释。史迪威恰好提供了一个现成答案。
坦率地说,我对这个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史迪威身后20年,美国碰到了另一个泥潭:越南。这次不仅仅是一个人饱受挫折与迷茫的折磨,而是一代人。在很多地方,两者很相似:罗斯福曾问蒋介石的为人,结果在史迪威和陈纳德那里得到两个对立的答案;越战时期,肯尼迪总统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以致他询问两位调查官员:“两位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这两次,美国都致力于实现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即当地军事上的自足;都遇到了一个固执专制、信奉基督教的当地领导人;局势也一样总是极坏。然而越战中,美军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史迪威当年的愿望:打碎这一该死的体制(但吴庭艳被推翻后南越状况却更糟了)、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但却陷入了泥潭),由于过多地依赖美国这个保护人,最终也腐蚀掉了南越的民族尊严。
塔奇曼这本书在越战最激烈的1971年写成,虽然没提到一句越南,但在当时深陷越战泥潭的气氛下,一个美国读者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同在东方的越南。假如史迪威能活着看到越战的结局,恐怕他也会重新考虑自己当初对中国以及蒋介石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