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曾有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早恋》、《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青春回旋曲》,报告文学《和当代中学生对话》、《和当代中学生通信》。近著有《音乐笔记》、《音乐的隔膜》、《聆听与吟唱》、《浪漫的丧失》、《纸的生命》、《遥远的含蓄》等。曾经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向往奥运》、《荔枝》、《银色的心愿》、《寻找贝多芬》等篇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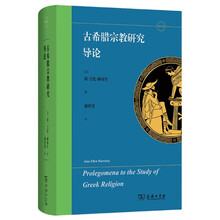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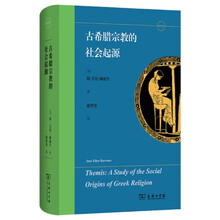








八大胡同是一种泛指。北京人对数字崇拜,讲究个“八”字,特别愿意用一个“八”字,雅的有燕京八景,俗的有天桥八大怪。这个“八”字只是一个虚数,就像李白诗中说的“疑是银河落九天”里“九”字一样。八大胡同泛指大栅栏一带的烟花柳巷而已,用当时《顺天时报丛谈》中的话说是“红楼碧户,舞扇歌衫”,和西洋人的红灯区一个意思。
不过,八大胡同的地理范围是有特指的,它们的方向在大栅栏西南,但到了南面的珠市口西大街为止,珠市口西大街是一道明显的界限。在老北京,这条街有无形的分水岭的地理标志作用,它以南属于低等档次,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八大胡同里的妓院虽然也有三四等甚至暗娼,但与一街之隔的铺陈市、四圣庙、花枝胡同里的老妈堂、暗门子下等妓院,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当时,逛八大胡同,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其意义有时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寻花问柳,而是有一种娱乐圈乃至社交圈的更为宽泛的意思在,超越情色之上,称之为泛娱乐化或泛情色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当年军阀曹锟贿选,袁世凯宴请,都是选择到八大胡同。
如今,在前门一带转悠,你常常会碰见如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些拉三轮的车夫祥子们,拦住你的去路,拉着你的胳膊,指着他们的三轮车车身上贴着的花花绿绿的照片,热情地对你说拉你到八大胡同转转吧。
八大胡同,在北京名气不小,特别是这几年,前门地区面临着拆迁,推土机日益轰鸣,位于前门地区的八大胡同命运未卜,从前朝阴影里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不容易,可是,说没,没准儿就没了,也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北京的,外地的,甚至外国的,拿着地图,特意到八大胡同来转悠的人增多,败落而凄清的八大胡同,比以前还要透着热闹。
娼妓制度,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一座城市,在过去的年代里,有妓院,就会有红灯区,妓院作为一种生意存在,便和任何生意一样,都是喜欢扎堆儿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规模化发展,生意才能够红火。在老北京的历史里,前门地区的八大胡同,只能够算做红灯区的后起之秀。最早出现的妓院在元朝,不过,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花胡同”和“锦胡同”,倒是已经在元杂剧之中出现,但不知具体指的哪些条胡同,即便有特指,那些胡同早已不复存在了。那时也有“勾栏”字眼的出现,不过,那时的勾栏指的是民间唱戏说书演杂耍的地方,类似现在我们的庙会,并不是后来的妓院的别称。因此,“花胡同”、“锦胡同”到底是妓院丛生的地方,还是勾栏集中的地方,应该存疑。不过,元代红灯区在北京肯定是存在的,据学者推测,那时的红灯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内城的西城和北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四附近。学者张清常教授就持这一说。
当然,这一说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北京城在元朝开始出现了街巷,北京现存的最老的胡同砖塔胡同,就是元朝的老街巷,在西四以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和张恨水先生都曾经住过那里。在元朝时,砖塔胡同是一条非常繁华热闹的胡同,那一带,勾栏瓦舍,歌舞升平,常常是关汉卿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他的戏剧演出的好场所,来这里的人常常可以看到他。那附近出现红灯区,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情。现在还存在的粉子胡同和花枝巷(都在砖塔胡同南,很近),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遗存。而砖塔胡同肯定是当时最热闹的红灯区中心地带。
据马可?波罗在他的笔记中记载,元大都当时有妓女两万五千名,和今天相比,这个数字肯定不算多,但在当时,确实不算少,那时京城里的人才有多少呀!这两万五千名妓女,可不是暗娼,或站街女,或发廊妹,那时的妓女,大多是艺伎。当时,每百名妓女,各设一名官吏管理;每千名妓女,再设一名更高层的官吏管理,如此有序的管理,为的是迎送外国使节,挑选上等妓女作为款待。这说明元代国家强盛的气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说明元代的风尚;也说明元代对妓女的管理真是舍得花气力,远远胜过后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放任和泛滥。
妓院和红灯区在北京真正出现,是在明朝,主要集中在内城的东城,已经从元朝的西边转移到东边了。这样区域性的整体移动,和东边的商业发达相关,当时就有“东富西贵”一说,即东城商人多而富庶,西城官员多而高贵。妓院移至东城,并非西城的官员就不狎妓玩乐,而是他们和任何政治制度之下的官员一样,都要拘着点儿面子,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却也要正襟危坐,所谓君子远庖厨一般,便让那些妓院都开在离自己稍远的东城,商人近水楼台,更让娱乐业促进自己的商业,两相发展,彼此得益而如鱼得水。可以说,这是自有妓院和红灯区的历史以来,一种普遍的经济规律。
张清常先生曾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考证:“明朝街巷名称中的红灯区有:勾栏胡同、本司(教坊司,清代笔记把它视同勾栏)胡同、粉子胡同、东院、西院、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勾栏胡同于民国改为内务部街,今沿用。东院、马姑娘胡同早已消失。西院全名为西院勾栏胡同,今大院胡同、小院胡同、小院西巷。宋姑娘胡同,今东西颂平胡同。本司胡同、粉子胡同仍在。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
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某些北京胡同,确实如张清常先生所说,是“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在清朝有所变化和发展。老北京的胡同名字,特别和妓院关系密切的,有这样几种:
一是勾栏:这是由唱戏的专有名词延伸出来的,自古以来,戏子是和妓女一样地位低下的,即使到了清朝,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那些曾经名扬一世的名角,当时都是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和妓女为邻。勾栏和妓院,便一直关系暧昧,如勾栏胡同、西院勾栏胡同,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是粉子:张清常先生解释粉子同本司,是教坊司,和勾栏一个意思。民间的解释,更为通俗,有好几个老大爷告诉我,粉子,就是脂粉的意思。清东城有分司厅胡同,是粉子的音的传讹,因为过去的朝代里,有教坊司一说,并没有分司厅这样的衙门口。
三是院:也是妓院的别称,比如当时著名的西院东院。当然,现在中国社科院的旧址贡院,另当别说,那是过去朝代礼部的遗迹,虽也叫院,和我们这里所说的院不一样。
四是姑娘:那时候叫姑娘,就和如今称呼小姐一样暧昧,凡带姑娘字眼的胡同,一般都和妓院有关,比如宋姑娘胡同、马姑娘胡同、马香儿胡同、乔英家桥等。而且这些带姓氏的胡同,据说当年都曾经有这个姓氏的名妓居住过。不过,张清常先生说的宋姑娘胡同,指的是现在的东西颂平胡同,在老北京,还有另一条宋姑娘胡同,在我小时候的住家附近,位于东打磨厂和巾帽胡同之间,离崇文门不远。那是一条有些弯曲的小胡同,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条胡同里,我常常到他家玩。那时的老街坊还常常鬼鬼祟祟地议论,那里曾经是娼寮之地,似乎还有她们的后代在那里住着一样。大概为了和东西颂平胡同的宋姑娘胡同区别,这里改叫过送姑娘胡同,一为“宋”氏的名词,一为“送”的动词,北京人的智慧大着呢,不尽的含义都在那里面了。有意思的是,为了对称,它的北段改成叫接姑娘胡同。文化大革命前夕,觉得这“宋”呀“送”呀“接”的都不好听,索性改成了莲子西巷。过去岁月里那些沧桑与故事,便这样被阉割了,如今,因为修新世界商厦和祈年大道,它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五是堂子:堂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和四大徽班进京有关,那时名伶的私寓,称之为“堂子”,名伶除台上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私寓教授弟子,接待客人,以及从事侍宴侑酒等有偿服务,便有了“相公”之说。“相公”一词的前身,便是“歌郎”。梅兰芳年幼时随朱小芬学戏,便当过这样的“歌郎”,号称“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朱小芬的私寓,便叫“云和堂”;而梅兰芳位于李铁拐斜街的祖居,即祖父梅巧玲的私寓,叫做“景和堂”,都曾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堂子。一直到光绪末年,堂子在八大胡同越发地畸形兴旺,成为了妓院一种暧昧的别称。另一种说法,堂子是南方对妓院的叫法,明初皇都移至京城之后,南方人大量移居北京,就和金陵便宜坊烤鸭移到了米市胡同开张一样,不少妓院也移到北京,在胡同里扎下根,便将那里的胡同改叫成了堂子。据说,明朝时京城一共有六条叫堂子的胡同,如赵堂子胡同,解放以后还在。崇文区花市一带的上堂子胡同,我读中学的时候天天从它身旁路过,一直挺立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不知算不算在这样的南方堂子之列。在崇文门内东单以南,建国以后一直还在的镇江胡同、苏州胡同,是明显带有明朝南方移民的痕迹的,而明朝就有的那六条堂子胡同,有四条就在苏州胡同以北。那时这一带是北京城的城边了,出了崇文门,就是荒郊野外。我猜想,这大概和最初南方妓女刚刚来京时人生地不熟,一要扎堆儿居住地界便宜,二为南方人服务和照料方便相关,就和现在北京城边的“浙江村”道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