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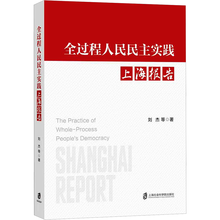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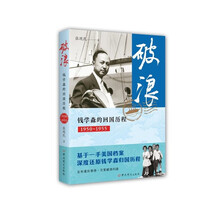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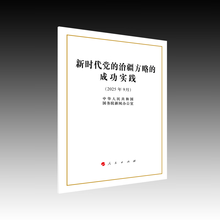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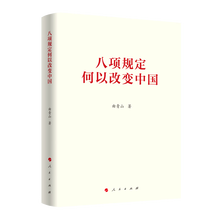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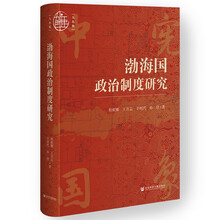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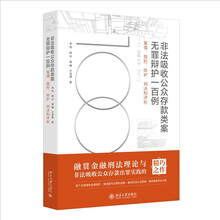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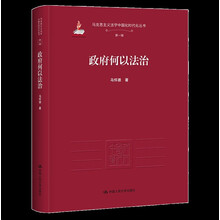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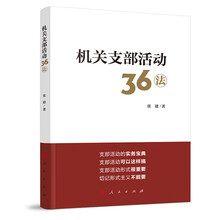
“江右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干、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驷、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缵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留日学生群体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
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文社科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经过80年代的激越蹈厉、90年代的沉潜蕴积,中国学术正在深入精进,这套“鹅湖学术丛书”即以此繁荣学术为念。这套丛书以“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为原则,有别于充斥坊间的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了重复堆垛而毫无创新的学术泡沫。
“开国会,为宪政上第一重大之事”。早在1903年中国人学习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就有留日学生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岛国,变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争雄的强国,“百废俱兴,新猷焕发,莫不本于宪法与国会之灵”。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了日本强盛的本源所在,认为中国学习日本,应当抓住这一核心问题。然而,由于1901年至1906年清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宣布“预备立宪”,加上受当时颇为流行的“国民程度不足”理论的影响,使得留日学生中之主张改革者,纷纷将目光投向清廷。他们积极参加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而在施行宪政方面,并没有抓住实质性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促使清廷实行。他们为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喝彩叫好,以为“我国自今以往,其必变专制而为立宪,已丝毫无所容疑”。
1906年底的官制改革,是主张立宪者试图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从而削弱皇权,实行君主立宪的初步尝试。它虽然抓住了君主立宪的一个重要问题,但那不过是进入政府的少数留日学生,依靠政府内部分主张立宪的官僚而进行的,而且他们的思想与其他众多主张立宪的留日学生一样,并没有突破“预备立宪”的框框。
官制改革的结果,使主张君主立宪者大失所望。此后,由留日学生创办或担任主笔、宣传君主立宪的刊物如《东方杂志》、《中国新报》、《政论》、《大同报》、《新译界》、《牖报》、《新译界》、《预备立宪公会报》、《宪政新志》、《法政杂志》、《国民公报》等等,均发生了舆论上的大转向。他们由对清廷预备立宪的热烈欢呼,转变为对其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批判;由依靠朝廷变革,转向依靠国民和立宪派自身的努力;由空泛的要求立宪,到提出明确目标--速开国会。在舆论大转向的过程中,杨度成为国会请愿的首倡者。
……
编辑人语
自序
绪论
第一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筹备立宪
一 筹备立宪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 宪政编查馆的中坚
三 草拟筹备立宪法规
四 谘议局的活跃分子
五 资政院的主角
六 发起组织国会请愿运动
第二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教育改革
一 对新学制及教育宗旨的影响
二 参与教育行政改革与教育发展规划
三 创办新式学堂
四 师资结构的变化
五 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革新
六 学堂的重要管理者
第三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军编练
一 规划全国新军编练
二 督导各地新军建设
三 新型军官群体
四 军事教育的骨干
五 筹划军事操演
第四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法制变革
一 译介东西方法律
二 编纂新律
三 与礼教派的斗争
四 参与司法体制变革
结束语
附录 晚清留学生任用状况分析
附表
一 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及参随人员出身表
二 宪政编查馆职员衔名及出身表
三 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姓名及出身表
四 资政院议员衔名及出身表
五 清末主要官办学堂管理人员出身表
六 清末新军统制及统领出身表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