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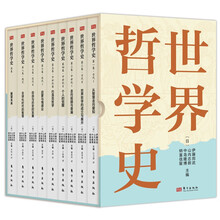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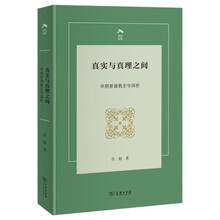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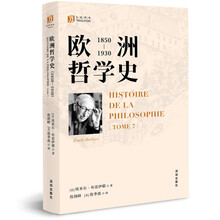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哲学已经发育成规模颇大的雏形。但并没有进一步地繁衍出中国的马克思,甚至把我们古代的哲学文化系统分类,也就是我国一位争议颇大的哲学大家于1986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中国哲学史的《史记》,更是中国哲学学者们不可漏读的教本。
说《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中国古哲学的《史记》,是因为它抛弃了流水账的记事方式,以时间为序,以人物,事件为纲,赋予古代哲学史以鲜活的血液,灵动的筋骨……否定-肯定-再否定。这是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古代哲学在这规律下逐渐成长。《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细述了,汉初到魏晋,中国古代哲学的转变历程:汉初,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哲学思想趋近于休养生息的安民之道。贾谊-汉初最大的政论家和哲学家提出恢复"理""法"的哲学论调;董仲舒公羊学开始宣扬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哲学家刘歆。杨雄及恒谭共同带领古文经学的兴起;王充-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更是地位显赫……魏晋时代起,玄学历经三阶段的发展,走向落幕;佛学在古代中国有着类似的发展历程,从传入到后来蓬勃发展的三个阶段:"格义","教门"和"宗教",隋唐的佛学向宋明的道学过渡……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他从十八岁就开始政治和学术活动,三十三岁就死了。在十五年中他对当时各方面的重大问题,都作了分析并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成为后来汉朝的统治者制订政策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现有的《贾谊新书》大半是从《汉书》割裂下来的,不一定是原来的58篇,但还是研究贾谊思想的主要材料。(以下引《新书》据卢文弨校本。)
贾谊《过秦论》在《史记》中不分篇,《新书》分之为上、下篇,后来又有人分之为上、中、下三篇。
照《新书》所编排的《过秦论》上篇论秦始皇,把秦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下篇继续对于攻守异势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秦始皇的统一全中国的政策,是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因为原来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之下,各诸侯国“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秦朝灭了六国,把全中国置于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老百姓都希望从此以后可以不打仗了,可以平安过日子了。这是一种形势。贾谊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新书·过秦论下》这里所说的“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就是陆贾所说的“逆取、顺守”。取与守的方法是不同的。秦朝在用诈力取天下之后应该改用守的方法,可是秦朝没有改,所以就很快地灭亡了。
陆贾和贾谊的这种意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是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而且应该用暴力。在得到政权统一全中国以巩固政权的时候,也可以而且应该用暴力。但是,在政权已经巩固以后,就应该用另外一种方法对付老百姓。就是说,对付奴隶主阶级和敌国可以用暴力消灭它,可是对付老百姓专凭那一手就不行。
汉高祖的《大风歌》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也知道在他已经掌握了统治权以后,问题在于怎么样守住政权。陆贾和贾谊也都说,要注重“守”,并且提出了“守”的方法。这就回答了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在农民起义面前所要面临的问题。
陆贾和贾谊虽然都批判了秦朝,但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那样,完全否定秦朝对于历史的贡献。他们只是说,秦朝所以先成功而后失败,这主要是由于在它统一全中国以前和以后的形势不同。形势不同,应付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在“取”的时候,秦朝用的方法对了,所以成功。在“守”的时候,秦朝不知道要改变方法,方法用错了,所以失败。
刘向(公元前79——公元8年)和他的儿子刘歆(死于公元10年)都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在许多学术工作中,刘歆完成了刘向的事业。
汉朝有几个有名的父子。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都是父子相传,在学术上作出贡献。班固继承他父亲班彪的事业,完成了《汉书》。这部书记载西汉一个朝代的
历史学术和典章制度。其中有三个志,都是照抄刘向和刘歆的著作。
刘向生在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家族。他的先祖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就是说,他们四个学生,都没有毕业就散了。到高祖的时候,浮邱伯到长安,刘交派他的儿子郢客和申公到长安,向浮邱伯继续学习,直至毕业。申公为《诗》作《传》,号为《鲁诗》。刘交也为《诗》作《传》,号《元王诗》。刘交的后人刘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他的儿子刘德,“少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以上引文见《汉书·楚元王传》)。刘德就是刘向的父亲。这个家族,虽然也是汉朝的宗室,但有一个学术传统,可以上接荀况及黄老。班固作《汉书》,把刘向、刘歆的传附于刘交的传后,统称之曰《楚元王传》,大概还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血统相传。
《汉书·刘向传》说:“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洪范五行传记》)。刘向作这部书的目的,是警诫成帝,叫他不要过于信任王凤;这是有为而发的。《汉书》的《五行志》,就是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为其基本内容。
在《汉书·五行志》中,有“经”,有“传”,有“说”,又有“刘向以为”,“刘歆以为”等。“经”是《洪范》原文。“传”是汉初经学家伏胜所作的《洪范五行传》。“说”是当时“博士”的解释。“刘向以为”等是刘向等的推论比附。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主要的就是这些推论比附。
刘向的书,把可能有的政治上的错误分成许多类,把可能有的灾异也分成许多类,然后把这两类本来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出现了某类灾异,就是由于政治上有了某类的错误。这就是所谓“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刘向又把从春秋以来出现的灾异和当时政治上的错误联系起来,作为对照,以证明这些说法的正确。这就是所谓“连传祸福,著其占验”。刘向的《五行传论》可以说是一种灾异大全,是汉朝“天人感应”的思想的百科全书。
《汉书·五行志》说,刘歆的《五行传》,跟刘向的《五行传》很有不同。照《五行志》所记载的,那些不同,都是细节不同,不是原则性的不同。在这一方面,刘歆也还是宣传“天人感应”。
这是向、歆父子的第一期的著作。对于刘歆说,这是他早期的著作。
王充肯定,客观实在是认识的对象和是非的标准;这就是他所说的“实”。在第一节中,我们讲过,王充自述他的著作的目的是“考论实虚”(《自纪》)。世俗有许多没有“实”作根据的言论。这种言论就是“虚”,也就是“妄”。王充说,他作《论衡》的目的,就是“疾虚妄”。所以《论衡》称为“实论”。《论衡》中各篇常叙述当时各种虚妄言论,然后以“如实论之”,或“实者”,提出他的批判。他认为,他的批判都是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的。合乎事实的为是;违反事实的为非。这是王充的认识论的基本的唯物主义精神。
《论衡》中有《实知》和《知实》两篇。从这篇名可以看出王充重视认识和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必以客观实在为对象;这就是所谓“知实”。真正的认识必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知实”);这就是所谓“实知”。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在跟当时谶纬迷信所宣扬的神秘主义思想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实知》和《知实》两篇中,王充着重指出,圣人并不是神怪,并不能“前知”;孔丘是圣人,不是神怪。他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正圣刁则神矣;若蓍、龟之知吉凶,蓍草称神,龟称灵矣。贤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谓之贤。夫名异则实殊,质同则称钧。以圣名论之,知圣人卓绝,与贤殊也。”(《实知》)这里所谓“儒者”就是董仲舒以及后来的谶纬家。他们认为圣就是神,有超自然的能力,能知生前、死后之事。圣人是超人;贤人是人。圣与贤有质的不同。
王充引当时儒者的话说:“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上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乱我书。’”(同上)这是说,孔丘预先知道后来有个秦始皇作“焚书坑儒”之事;还预先知道有个董仲舒整理(“乱”)他的经典。这就是说,孔丘预先知道后来儒家的废典。王充指出,这些都是虚言,不可信。在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谶记的虚妄是一望而知的。但是,在王充的时候,谶纬思想正占统治的地位。王充在他的著作中,正式指出谶纬的虚妄,这是有极大的斗争意义的。
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作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各方面进行辩论,由此推动哲学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玄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般和特殊的问题。玄学进人尾声以后,随着佛教影响扩大,作为时代思潮的中心问题也换了。这个新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生死、形神的问题。
恩格斯说:“在远古的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人的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20页)
这种人的精神和人的肉体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称为形神问题,从战国以来经常为人们所讨论,是一般人都关心的问题。
……
绪论
第二十五章 汉初黄老之学
第二十六章 汉初最大的政论家和哲学家——贾谊
第二十七章 董仲舒公羊学和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
第二十八章 《礼记》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第二十九章 董仲舒哲学体系的对立面——淮南王刘安的黄老之学
第三十章 《盐铁论》与“义利之辨”
第三十一章 纬书中的世界图式
第三十二章 古文学的兴起及其哲学家——刘歆、扬雄、桓谭
第三十三章 王充——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三十四章 东汉末无神论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三十五章 东汉末农民起义和《太平经》
第四册 自序
第四册 绪论
第三十六章 玄学的先河——刘劭的《人物志》和钟会的《四本论》
第三十七章 通论玄学
第三十八章 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玄学的建立及其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三十九章 嵇康、阮籍及其他“竹林名士”
第四十章 裴頠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四十一章 郭象的“无无论”——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第四十二章 魏晋之际玄学以外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四十三章 玄学的尾声及其历史的功过
第四十四章 通论佛学
第四十五章 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格义”
第四十六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教门
第四十七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宗门”
第四十八章 隋唐佛学向宋明道学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