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来港,轰动了全香港。然而,就在典礼举行之前一个月,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卦。负责撰写和宣读赞词的教授,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突然通知大学,说几经郑重考虑,认为由于个人身份与意见的缘故,自己不宜担任这一荣誉性的工作,请求另觅人选。在仓促之中,这令校方感到极端尴尬,最后决定,由我替补。
由于当时社会上对巴老有各种不同评价,所以撰写赞词是一桩相当敏感的工作;更何况,我虽然对文学有兴趣,也曾在报章和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字,但却从来没有字斟句酌地撰写过经得起推敲,可以当众诵读的文章。此外,在这典礼上一共有四篇不同的赞词以及相应的英译稿都要由我一个人负责,所以足足有三四个星期之久我抛开了一切日常事务,日以继夜地赶工,饶是如此,也只是到最后一刻钟才完成工作。但辛劳没有白费:典礼过后,这几篇文章引起了颇大注意和反响,有的报章将四篇赞词全文转载,有些前辈学者表示欣赏,甚至巴老也含蓄地说:“看来陈先生对我是有了解的。”由是我认识了巴老和王元化先生,以后每到上海总要前往拜望;陪伴巴老来港的陈丹晨兄也成了好朋友,时相往还。就这样,由于一个偶然机遇,我开始和中学时代所曾深深爱好的笔墨工作重续前缘。
然而,整整十年之后,我才知道巴老当时那句淡淡的说话委实是太宽大太慷慨了。1993年丹晨兄送我他的新作《巴金的梦——巴金的前半生》,其后又读到陈思和的《巴金传:人格的发展),这才如梦初醒,初次意识到青年巴金底子里其实是一位热烈、真诚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走上文学道路只是后来偶然的事;这才汗流浃背,深深感到我这篇赞词的浮泛。由是,对历史之复杂、曲折,和知人论世之艰难,我得到了更真切的体会。
1985年我在中文大学秘书处工作已经五年,当时马临校长年届六十,本有意退休。但当时香港政治地位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由于各方恳请,他终于勉为其难,宣布接受校董会的邀请再延任两年,即至1987年为止。我则觉得,这正是自己结束行政工作,趁早返回学术领域的时候了。不过我离开物理系已多年,虽然经常和系里保持密切联系,要立即再展开已经搁下的研究工作自然不免吃力,因此颇为感到犹豫。
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年冬天,已届八十高龄的小国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郑德坤教授因为中风而住院,看样子势不能再回研究所。由于我对文史有很深兴趣,又曾经和研究的同事略有往还,因此就动了念头,向校方提出,请求改调研究所的空缺。这是个大胆,超越常规的请求。大学当局多方谘询,所得意见好像并不一致,几经踌躇之下,才决定破格接纳所请。其所以能通过,可能与历届所长或由校长本人兼任,或由访问教授、退休教授担任,迄无定制有关;但据闻所内一位前辈学者的颔首,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1986年1月26日,接近九十高龄的父亲逝世。他平生笃实勤奋,有为有守,说话不多,但以言行身教,对我做人为学,发生极大影响。他的离去,是个沉重打击,使我顿时意识到生命已进入完全不同的阶段。同年8月,我离开繁忙的秘书处,搬到离行政楼只不过三十米之遥,然而却幽雅安静得多的四合院式中国文化研究所去,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尝试。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传统政治开始崩坏。崩坏的十分复杂,但最基本的则是:第一,由于宗教革命,教会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作为传统政治基石的普世性原则动摇乃至崩溃;第二,16世纪的远洋航行、军事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兴起扩张了国家活动空间,增加了国际竞争频率和强度,从而令国家内部民众动员的需要剧化。这样,就打破了上述普世性与各别性原则通过习惯、传统而建立的依存关系和各自有效范围,驱动各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
普世性原则丧失约束力,以及长期和大量的民众动员可以说是近代欧洲政治嬗变的两个主要趋势,而其自然结果,则是体现民族特性的个别性原则的重要性增加,乃至“普世化”。在很大程度上,这就造成了民族主义诞生的环境。
由于白话文的出现,传统语、文分家的现象大体结束,我们也找到了建设现代国家所急切需要的民族语言。然而,中国的语文问题是否就已经圆满解决了呢?只要稍为反省一下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发展,我们就会看到,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中国目前正面临另一种语文危机,它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但其严重性也许不下于本世纪初。
在本世纪初,中国的大问题是排满与革命,是建设一个能团结民众、抵御外侮的民族国家;相应的语文问题是沟通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以及输入现代观念;而答案则是早已经广泛潜存于民间的白话。胡适、陈独秀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应用它、发挥它、提倡它,从理论上宣传它的重要性而已。在今日,在21世纪行将来,临的时候,中国的大问题却是全球化,是在商业、科技、文化等各个层面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全面竞争。这种竞争所需要的,已不复是单纯的民族团结或者自律、自励,而是民族中每一个人的潜能、才华之充分发挥。所以,相应的语文问题变为:如何令中文成为在科技、医药、法律、财经、会计、商业、航空、外贸等各个层面都可以充分和广泛地运用的语言——在今日全球化格局之下,也就是成为主要国际语言,与英语抗衡。
很明显,在目前甚至今后数十年内,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上的重大差距,要中文与英语分庭抗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也许免不了会有这样一种疑问:如所周知,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能力很强,很能够充分适应以英语作为惟一国际语言的环境。那么真有必要争胜好强,去为中文勉强争取国际地位吗?事实上,以中国人口之众多,发展潜力之雄厚,只要能把国民总产值增加一个数量级,则中文地位之提升,将是水到渠成,再也自然不过的事。目前去为这问题伤脑筋,是既不实际也无必要的。
这样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但也不很深入。首先,接受另一种语言作为强势国际语言,对整个民族而言,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只要稍为想一下,全中国十数亿人口之中,从小学以至大学本科和研究院那无数学生为学习外语,为准备托福考试而付出了多少精力、时间,而忍受了多少煎熬、苦恼,就会知道问题是何等严重了。是中国人的聪明、勤劳无可置疑,然而,由于要克服母语与国际语言之间的隔膜,这聪明、勤劳的实质发挥恐怕最少得打上个七折八扣,那是无可否认的。所以尽早促使中文变为主要国际语言并非是为虚荣,而是具有极大实际迫切性的事。
很明显,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潮在下一世纪将愈发高涨,这浪潮是与西方国家所主导和竭力推动的政治与文化整合密切相关的。整个东亚,从日本到中国,都已经先后完全认同这一体化与整合的大趋势。运输和资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超高速船舶、超大载量喷射客机,以及所谓资讯超级公路的出现)将会为这个趋势的加速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其结果则是目前已经萌芽的全球性商品与文化市场之深化与持续扩展。
在这市场中,传统文化显然不会消失,而是被肢解和重新包装、组合,以适应大众口味和心理需要。老子、佛祖、织田信长、禅和加缪、凡高、贝多芬等等人物、思想、影像、乐音在电脑网络、电视屏幕上,和普及书籍、光碟中,以不同形态、方式出现亿千万次,成为个人各凭喜好选择的精神冷饮和快餐。当然,也还会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文化、艺术社团,为各种理念、爱好提供服务,或者作政治鼓吹,从而发挥某种影响力。这可以说是支离(atomized)文化与支离社群(乃至个人)的结合。
在更高层次,国家仍然会通过国民教育和报纸、杂志等煤介来维持其传统文化的有限度独特和独立性。这种系统和整体性的文化结构饱受市场文化冲击和侵蚀,但最少就东方文化而言,大致不可能在下一世纪消失。这主要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首先,是中国和日本的庞大人口;其次,是语言、文化在集体记忆中的巨大惰性——人的智力成长与学习过程缓慢,因此这记忆不可能在三五十年间全面改变;最后,人在心理上仍然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具体、形象化的环境,而传统文化则正好充当人与抽象、理性化的现代世界之间的缓冲界面。
因此,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或更应当说是现代文明)可能仍然要经历相当一段并存和交互渗透的时期。20世纪是这个时期的开始,它的结束是否就在21世纪?从以下几个发展看来,这可能性是存在的。首先,是英语迅速取代其他语言成为国际性语言,并且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基础教育的核心部分;全球经济运作,也同样以英语为基础。更重要的,则是人工智能研究,特别是自然语言的分析、翻译和其他应用之不断进展。这方面的工作很艰巨,但正如分子生物研究一样,经过长期努力和电脑不断改进之后,很可能就会出现突破性迅猛发呢。今后三五十年内,人工智能研究达到这个转折点是可以预期的。届时这突破与全球资讯网络结合,从而对人类思维乃至自我意识产生的强大冲击,恐怕将远远超过今日所能想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不可能再循原有形式立足。在最基本层面,它必须走到电子煤体——电脑记忆体、网络、光碟等等之上,以资料库、电视系列、屏幕影像乃至电子游戏的方式出现,才可能有效率地在一般人意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从口语相传到纪录在竹木、纸张上是一次革命,现在第二次载体革命已经来临,它对所有传统文化都必然产生空前严峻的淘汰、提炼作用。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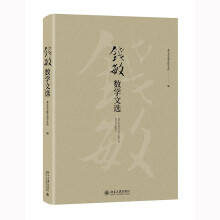



十五年前,我离开曾经从事二十年之久的物理专业本行,以及后来担任了六年的行政职务,转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这无疑是个巨大转向,但揆诸许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曾经历的曲折道路,前例尽多的是,算不上有什么特别。到研究所之后,我所最着力推动的,便是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本来,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在1967年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之初,便已经提出“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这一理想,作为它的长远目标。然而,由于种种缘故,研究所其后的发展却逐渐集中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文物与艺术方面。因此,到了80年代末叶,近代中国研究实际上必须从头开始,这对于像我这样“转行”的人来说,自然十分吃力。幸运的是,研究所提供了自由的环境和各种资源,使得我和几位志趣相近的同事能够合作开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成立“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开好几个学术研讨会,还出版若干种丛书,在十多年光阴里为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探讨营奠了一个环境。
这本集子所收将近五十篇文字,便是我到研究所之后,在上述意念推动下陆陆续续写出来的作品,其中部分与特殊场合、刊物有关,但大部分则是围绕着现代化探讨这一主题而衍生。何谓“现代”,自然有许多不同说法。我认为也许最能凸显其特质的,则是其断裂性以及相因而至的纷杂性、变动性。李校长的格言,触及了这断裂性在时间以及空间的两个向度;史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之说,则从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分野,指出西方文化内部的断裂;而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踏入的这一个以生物之复制,人类基因库之解码,以及电脑能力之爆炸性扩张为标志的“美妙新世纪”,与刚刚结束的20世纪之间,无论从经济——社会结构抑或人类意识来说,亦同样有巨大鸿沟存乎其间。
由于“现代”的断裂特性,这本集子所收论文性质庞杂不齐,那并不足怪,甚且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表示,李卓敏校长的理想已经被遗忘,或者我没有做过一些跨越文化鸿沟的微弱努力——事实上,这恐怕是所有知识分子,无论在中国、西方抑或其他文明,虽然明知其不可也都无从逃避的一种尝试吧?20世纪之初,初次接触康德与叔本华的王国维便曾有“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之叹,乃至感到有“在二者之间”终其一生的危险。然则,对今日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桥飞架南北,天
堑变通途”的梦想恐怕更遥不可及了,倘若不甘以学术专业的深沟高垒自限,则以短暂生涯充填不同文化间沟壑之命运,殆将不免,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诚然,以十五年功夫,只得出这么一点儿成绩,虽谓纷繁事务间隙中草成,亦殊感汗颜。不过,敝帚自珍,人之常情,这些文字纵然空疏粗浅,自问倒也还用了心思,并非徒落窠臼,是耶非耶,识者正之。再次套用静安先生的话:“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至于他所向往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则恐非吾辈常人所能企及,只有“俟诸天之所为”了。
这本集子相烦沈昌文兄弟安排出版,冒渎王元化、杨振宁二位前辈先生清神赐序,有劳饶公挥笔题词,对他们的热心和爱护,我铭感于中,谨此深深拜谢。此外,李忠孝先生负责编辑,李洁儿小姐帮忙文字输入和打印,严桂香女士协助处理大量有关事务,都是我由衷感激的。最后,先你克文公自20年代初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以还,在剧变的大时代中从政、办报、办学、教书者前后凡六十年,终生孜矻勤奋,但言行身教的影响则无可估量,我以此集敬献于父亲,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
2001年9月18日于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