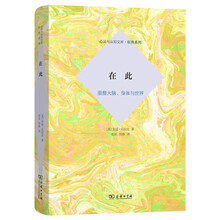有些哲学家在随后的方法中努力去克服困难,他们把较长时期内某种感觉的持续性看做是一种完全充足的标准,以此作为“有张桌子”这一命题的真理。他们的证据在于,有了“桌子”这一语词,我们只是想指明一种客体,这一客体导致了某种形式的视觉和触觉及其持续性。由于这就是我们通过“桌子”这一语词体会到的所有含义,如果列举的实验获得实现,那么桌子的存在就完全确定了。因此,根据实际的粒子类对具有不可怀疑性和绝对性的有形客体做出断言,这也是可能的,这就是我将用的论据,其主要目的是揭示(说明)感觉信息命题的极大确定性的逻辑源。
首先,我将对这个论据做适当的修正。这暗示了我们所指的是具有某种影响的客体,而不是由“桌子”这一语词所提及的其他客体(顺便提一下,人们应该注意到,基于所调查的事情的本质,这个论据与旧的论据具有语言上的平行性。得承认,说话的语言方式的转变有某种心理优势:人们更乐于准备去改变一种说话方式,而不是去承认不同于所假设的一种事情的本质。然而,瞧一瞧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进展,就会觉得很难判定是否语言运用理论比本质理论更具灵活性)。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和了解一直到现在我们称为“桌子”的事物也是万有引力之源,那么,我们几乎不能改变我们的设想。在测试有关桌子的断言中,我们没有丝毫理由不该利用万有引力的存在。当然,这个例子有点不实际,因为我们几乎不能涉及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为了证明桌子的存在,万有引力的测量将是一种比用肉眼和直接观察更为方便的方法。但就巨星体、类星体或者双星体的黑色伴星而言,这种情形正好相反。这里,万有引力的测量甚至可能是惟一可应用的方法。一旦我们成功地通过我们的感官对物质影响给出随机的生理上的解释,或者至少当我们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的感觉印象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感官通过介于其间的媒介所观察到的客体的随机影响,那么就不能再仅凭一点点借口而武断地依据感觉印象来对“桌子”一词的定义进行限制。我们就会知道这些感觉印象只是桌子对其周围物产生的一部分影响,而且我们知道这些影响只有通过大部分人各自对其熟悉而被区分开。此外,这样的定义会违反原则,不应该用特别的说明对争论中的现象进行解释。这是因为其结果是:用(“因为桌子在此”)这一命题(该陈述逻辑上等同于讨论中的事态的描述)来回答如下问题:我们感到一种抵抗以及我们有桌子样的视觉印象,那又会怎么样?
但是让我们设想哲学家自由地提出无感觉的定义,并因此让咱们允许哲学家给“桌子”下定义,以便某种感觉确定到桌子的存在!然后,我们仍然得说关于桌子命题的不容置疑将追溯到这样一个定义,该定义声称实验程序在某一阶段完成,该定义还宣称从现在起“桌子”的存在是肯定的。这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决定与习俗在所讨论的确定性中起重要作用。过后我们会发现,关于感觉信息命题被指称的不容置疑与绝对正确与其说是根据拥有感觉信息的本性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它影响到决定的结果。我们的讨论将与这些决定的实际性(practicality)有关,而且那就是感觉信息“存在”问题的所有线索(顺便提到,人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已经意识到上面给“桌子”引入的定义是很不实际的,它给某种感觉的表象带来特别的解释,而且这普遍适用于各种定义)。
但是,让咱们再回到桌子这一例子上。我们已经声明,对于保证一系列操作后的结果的确定性,这个例子是个很不实际的决定。然而,人们能够反对这点,理由是我们确信日常生活中“桌子就在我前面”这一命题的真实性,甚至不需要明确的定义。对此,一些哲学家解释道,我们无意识地信任某种定义,因为毕竟我们无意识地在某种很好地定义的意义上使用了“桌子”一词。我认为这一解释完全不现实,它假定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各种可能的、可设想的和不可设想的实验的反应做出长期的决定。头一次经历幻觉、完全的幻觉、有条理的幻想等等之类的设想的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承认这种设想是幻想。在语言应用的固有的内在的定义基础上,与其说他是镇静自若地解释他刚刚观察了一张不普通的桌子,倒不如说他只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回想时,哪怕他已经面临完全幻觉而且明白在发生什么,还会理所当然地坚持“桌子在此”这一命题。更重要的是,仅仅通过这个决定,这个命题才是确定的(根据在定义中起作用的证据),事先并不能确定(当然除了纯粹心理学意义上之外),这是因为后者会预先假定有人已经知道最终哪项决定将被接受。
我们将另外举例说明这一争论。据说,普通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使用“桌子”一词,结果他就据此对桌子的本性做出某些有明确性的假设。他不是以一种明确的定义的形式使这些显得很明白。相反,这些设想非常含蓄地包含在他的语言中,而且它们具有确定性。那么,桌子的本质是什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说桌子是我们和别人能够看见和触摸到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看见并触摸到像桌子样的东西,并且其他人经历了同样的感觉,那么,就毫不怀疑这是一张桌子。这一强烈信念的逻辑理由是什么呢?是否表明存在逻辑上不容置疑的命题?为了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咱们假定摄影师给桌子拍照片,而且,在底片上别无他物,只有空房以及二、三个人好像坐在桌子前面。咱们也可以假定无人知道摄影的本质。那么我们不会因为完全不相关而丢弃这张底片吧?这一态度是基于什么立场呢?我相信这一态度只是因为不知道(无知是福)。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例子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如此相信自己,以至我们相信判定与调查研究是不需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迫使我们做此决定的情景。这样,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命题的逻辑确定性问题仍旧完全敞开着,因为我们仍旧一点也不能理解。我们相信自己,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如此确信地主张的命题的绝对真实性甚至真理的背后根本就无物遵循。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