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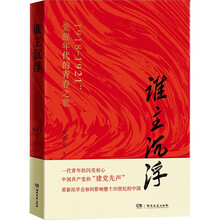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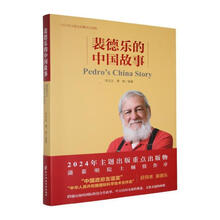








第一章 失踪
1953年10月一个暖和的星期天的早晨,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我的美女阿姨下床之后,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我听见她起床,估计她要到外头上厕所去,”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卜艾瑞姨夫这么告诉警长,“后来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等我再醒过来时,大概已经过了半个钟头,她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对自己说:‘还是去看看美女有没有事的好。’所以我就起床去看了。”
卜艾瑞姨夫是个矿工,美女阿姨和他们的儿子梧罗却住在老远的一个名叫“弯曲山脊”的地方。这山脊十分狭长,而且与世隔绝,就在弗吉尼亚州的加煤镇附近,正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陡峭与崎岖的地方。那时候的道路既狭窄又布满岩石,碰到坏天气的话,几乎无法通行。他们有一辆很旧的福特汽车,那天清晨,车子就停在斜坡上,车钥匙也如往常一样插在点火装置上。跟他们住得最近的邻居史家,也离他们有一英里之遥。史家人告诉
警长,并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根据卜艾瑞姨夫的说法,那天美女阿姨光着脚,身上也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衣。她的两双鞋和所有的衣服仍然放在原来的位置,完全没有离家出走或是胡闯乱逛到其他地方去的迹象。更何况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胡乱闲逛的,除非身穿睡衣的她赤脚越过那些荒无人烟的山丘。即使如此,住在另一头的人也一定会注意到她。可是到处都看不到新的足迹,连大门旁边湿软的地上也没有,卜艾瑞姨夫和睡在顶楼的梧罗都没有听见不寻常的声音。
我们镇上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因此,一旦消息传了出来,大家都震惊得不知所措。
“真是,谁听说过一个人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他们说。
“如果我们听到的是实情的话,”有人说,“一定会在什么地方的森林里发现尸体的。”
还有人说:“一定有人在下面不远的路上停了一辆车等着她,两人便一起坐车走了。”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天早上一定会有人听见车子上山的声音,是不是?”
“应该是。”
大家仍在臆测。
我妈妈好难过,她名叫杜小爱,是加煤镇高中的朗读与戏剧班的老师,也是失踪人的姐姐。她在《山中回声》的一篇访问中说,自己的妹妹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还不够糟吗?大家还非得四处嚼舌根,让已经很悲惨的状况变得更糟了。实在太过分了,她说,太过分了。外公与外婆,也就是妈妈与美女阿姨的父母本想让梧罗跟他们一起住,但是卜艾瑞姨夫怎么也不肯。
一天一天过去了,一星期又一星期也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等到几星期变成几个月的时候,山中的居民再度恢复了原来单调、乏味的生活,美女阿姨却像成了民间女英雄似的,有人甚至为她写了一首歌,在加煤镇最大的酒馆“忙碌的蜜蜂”里演唱着,由一支乡村蓝调乐队伴奏。不过妈妈严格禁止任何人在她面前唱那首歌,她说歌词里有强烈的影射意味。
美女阿姨失踪六个月之后,我们发现卜艾瑞姨夫一逮到机会,就满头满脑连着胡子都浸在酒里。
“真不是抚养小男孩的健康环境。”我外婆口口声声说道。
于是外婆坚持要带梧罗回她的家,这回卜艾瑞姨夫倒不反对。
当地的广播电台WCSV曾颇为自豪地宣称,说加煤镇是“煤矿区的心脏地带”,其实它只是一个建筑在黑河与矿渣溪汇流处的山间小镇,既肮脏又黯淡,不过是山丘之间的一块宽广的路面罢了。小镇的外缘是调车场,火车在那儿可以把全镇生产的煤运送到东部与北部的各个地点。这也是加煤镇名字的由来。
加煤镇只有两条街。顺着地势走,一条叫作大街,是所有商家坐落的地点,与黑河平行。还有一条叫住宅街,也是附近方圆几英里之内唯一可以盖房子时不必沿山坡建筑,也不会悬在山边的一条街道。
其实住宅街更是全镇最明亮的地方。在许多漂亮的房子当中,有一栋是我李姬赛和我妈妈与继父杜波特一起住的,他是《山中回声》的编辑。我们的房子是现代农庄式样的单层砖造住宅,有白色的百叶窗,一个前廊,还有全镇唯一的观景窗。我们有一部电话、两台收音机、一台唱机、一台冰箱、一个立式冰柜,以及一个电炉。住在我们隔壁的外公与外婆也有同样的便利设备,可是他们的两层楼房间更大也更老些,有绿色与白色的百叶窗,两层楼都有环绕的走廊。他们还有一台电视机,如果天气理想的话,偶尔可以看到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查士敦的节目,只是画面十分模糊而已。据外公说是因为山区的关系,影响到信号的接收。在我们两栋房子的四周是一大片赏心悦目的如茵草地,还有大约五十棵苹果树,我们管它叫果园。看见棵棵苹果树在春天的时候开满了花,是多么奇妙又欢欣的景象啊!此外还有杜鹃花,粉红
的、紫红的,更不用说还有溪边的紫丁香花丛,以及野生的山茱萸。经过我们家的人们有时走着走着会停下来,东瞧瞧、西看看,仿佛无法相信他们的眼睛似的。
梧罗搬来和我们同住的那年春天,我的世界大约就是这个模样。一切都是清新而明亮的,粉粉的、白白的。妈妈提醒我,说我多么得天独厚,又是多么幸运,除了偶尔有一个噩梦跑来纠缠我的时候之外,我丝毫不怀疑她的话。而做噩梦的时候我禁不住觉得自己并非得天独厚,而是深受其苦。这个梦和一头死去的动物有关,每次我总是哭着或尖叫着醒过来。
美女阿姨虽说是妈妈的亲妹妹,我却很少看到她或是她的儿子梧罗。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觉得她们两姐妹之间多年前似乎有过什么裂痕,可是我每次问妈
妈,她都说:“没有的事!我们很亲,很相爱的。”
我仍然很怀疑。
梧罗与他的父母亲住在老远的那个高高的山头,连自来水甚至冰箱都没有,而且他和我念的是不同的学校。我们一样年纪,我11月即将满12岁,他是那年1月什么时候就已经12岁了;我们也长得一般高,一般重:4英尺10英寸高,92磅重。但除此之外,我们简直没有一样像的地方,至少当时我知道的是这样。梧罗笨拙又土气,穿的是他爸与他爸的弟弟罗斯穿旧了的衣裤。我们
大概10岁的时候,有一回我看见梧罗穿的裤子实在太长,腰部也实在太肥,所以他拿一条绳子系在腰间,不让裤子掉下来。他那模样看起来真的滑稽极了。我想他也觉得很不自在,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穿了一件蓝色有皱边的连衣裙,一双黑色皮凉鞋。还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他头上戴了一顶过大的帽子,帽檐往下拉的话,可以遮住整个耳朵。他却为那丑丑的旧帽子骄傲得很。
我再告诉你关于梧罗的一些别的事——虽然我真的不想——他还是个斗眼。有时候你实在看不出他是不是在看你,而且他必须戴镜片很厚很厚的眼镜。
梧罗搬到隔壁的那个春天的晚上,我等不及要过去看他。我想知道他对他妈妈发生的事有没有什么不曾对人说的秘密或是想法。
那天是星期五,我身穿蓝色牛仔裤,坐在化妆台前的凳子上,让妈妈替我把金色的头发扎成两条长长的辫子。每当我有机会出去玩儿的时候,就喜欢把头发梳成这个样子,这也是我愿意忍受把头发留得那么长的唯一原因。
“好了,你别一过去就缠着他问美女阿姨的事,听到没有?”妈妈对我说。
“天哪!我又不是白痴。”我抗议道。
“很好,希望你不是。”她说,“他这些日子以来过得太苦了,我们应该多多体谅他,不要缠得他受不了。”
“缠他?你把我说得活像一只讨厌的蟑螂!”
妈妈哧哧地笑了。
“那就快去吧,去逗他开心。跟他说那个眼珠的笑话,那个笑话好滑稽,你又说得那么好。”
我有点儿自满。大家都知道我很会说笑话。妈妈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们对着镜子相视一笑。我妈妈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大家都这么说,而且她随时闻起来都好香——像圣诞节的糖果。她的头发总会让人想到那些柔柔亮亮的洗发精广告。
我溜下凳子,朝门口走过去。
“替我跟他打声招呼,说声欢迎。”妈妈在我身后喊道。
我飞快地跑过我们的院子去看梧罗。我发现那第一个黄昏,以及之后的许多黄昏,我都置身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苹果树上许多小小的花瓣撒在我身上,风将它们刮起来,并且让它们甜蜜的芳香在我的四周散发,使我走进大门之际晕乎乎的,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兴奋感觉。我大声跟外公、外婆打过招呼之后,立刻冲上楼梯,来到位于房子前方的梧罗的房间。
他蓬松的金发一直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于是他不断把头发甩到旁边。他正忙着把他少得可怜的东西收进镜
台的一个抽屉里。躺在床正中央的是外公的德国牧羊犬,它除了“狗狗”之外没有其他名字。它是一只很可爱的狗,大家都爱它。可是,如果让外婆看见狗狗大大咧咧地趴在床上,她就会大发脾气。梧罗该学的东西还真不少。
“嗨,邻居。”我说着扔给梧罗一块儿樱桃糖。
他接住了,然后注视着那块儿糖,仿佛它是金块儿似的。
“好呀!”他说。
我们俩都剥开了包装纸,再把糖果放进嘴里。我坐在床上,开始轻抚狗狗。它舔着我的手,我又搔它的耳后。然后它身子一滚,四爪朝天,好像是在说:“搔我的肚皮嘛,快嘛!”所以我就搔它的肚皮。它一只后腿开始抽动,我越是用力搔,它的腿也动得越快。
“梧罗,要不要听个笑话?”我说。
“好啊。”
他也坐上床,就坐在我和狗狗旁边。
“有一个人,”我说,“他走进一个啤酒馆,然后对老板说:‘我跟你赌一杯免费的啤酒,赌我可以咬住我的左眼珠。’
“酒馆老板笑着说:‘没有人可以咬到自己的眼珠。我赌了。’
“于是这个人摘下他的左眼珠咬在嘴里,再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那是一颗玻璃眼珠,你懂吗?
“结果酒馆里的人都快笑死了,那个人也免费喝了一杯啤酒。
“后来这个人又对酒馆老板说:‘我再跟你赌一杯啤酒,赌我可以咬到我的右眼珠。’
“‘什么!’那老板说,‘不可能!你不可能两颗眼珠都是玻璃的!赌了!’
“于是那人很快拿下他的假牙,再用假牙咬住他的右眼珠。”
这个笑话每回都管用,我觉得梧罗会笑成两半。
他的捧腹大笑将近结束之际,我正盘算着应该如何谈起他母亲的事,又不让他觉得我像蟑螂一样讨人厌。如果能够避免的话,我是不愿意去烦扰别人的,但是我却告诉自己,说不定这次真的避免不了。于是我耸耸肩,把妈妈的警告全部抛在了脑后,硬着头皮开口了:“梧罗,谈谈你妈妈的事。她究竟是怎么了?你八成有什么想法,是不是?”
“这……”
他用袖口抹了抹鼻子,什么也没说。我又试了一次。
“大人有时候好笨,是不是?他们总是看不见最重要的东西。”
梧罗默默点头同意,但是仍然什么也不说。
“我的意思是,梧罗,你不会不知道或是没注意到别人都没注意的事情吧?你难道没有什么事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想他们一定会笑你,因为你只是个小孩,你知道吗?”
“是啊,”梧罗突然说道,“是有一件事。”
他将他的斗鸡蓝眼珠转向我。我几乎一口吞下我的糖果,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会这么快就招了。
“什么事?”我说。
“我一直想跟爸爸谈那件事,可是他不肯听。”梧罗说。
然后,他走到他的抽屉柜前面,并且抽出一本书。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姬赛。”他悄声说道。
“这是什么?”我也变得小声起来。
“如果你答应做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告诉你。”他说。
“我会很荣幸的,梧罗!”我说,心中是真的高兴。
他的嘴一直咧到脸颊两边,露出大大的白牙齿和被樱桃糖染红了的舌头。他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我的手上。
映人我眼帘的是“一千首美丽的诗词”几个字。
“这本书是妈妈高中毕业时,外公送给她的礼物,” 梧罗说,“她喜欢极了。在她失踪前的几天,有一首诗她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把它背了下来。她把书像这样紧紧地捧着……”
梧罗把书拿回去,示范着把书捧在胸前的模样。
“而且她露出一种好奇妙的神情,望着外面的山丘——不,越过了山,甚至越过了地球——她就念着这首诗。在第88页上。”
他把书递给我,我飞快翻到88页。诗是这么写的:黎明的清风有秘密要告诉你。
别又睡着了。
你必须问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别又睡着了。
人们来来回回跨过门槛,
那是两个世界交会之处。
圆圆的门是开敞的。
别又睡着了。
——加拉路汀,13世纪波斯诗人
“这是什么意思,梧罗?”我悄声问道。
“你不懂吗?”他说。
然后他靠近我,用手指掠过他所读的字句。
“‘黎明的清风有秘密要告诉你’,”他念着,“她知道!她知道有什么事会在黎明的时候发生。”
“可是,是什么事呢?”我问。
“然后这首诗又说,‘别又睡着了’。所以她就没有回去睡。她起床后就出去了。”
“后来呢,梧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他说,“我就是不知道。”
“就这样?”我好失望地说。
“是啊,”他说话的口气很悲伤,“我只知道这些。她一大早起床就出去了,因为她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见到她了。”
他合上书,紧紧捧在心口上。
“可是一切都在这里,”他神秘兮兮地悄悄说道,“秘密就藏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
第二章 爸爸、妈妈和阿姨
“你为什么替她取名叫‘美女’啊?”次日上午,我对外婆大声喊道。
我这么大声叫,是因为她与外公两个都已经有些耳背,却又都顽固地不肯戴助听器。因此在他们的房子里,大家都是这么大声嚷嚷。我们已经习惯了,连登门拜访的客人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美女’是很好的名字啊!”外婆说。
我们俩在她那又大又通风的黄色厨房为我继父的生日蛋糕做最后修饰。我继父和妈妈到阿平登去看他的几个亲戚,外公与梧罗两人出去买衣服了。这倒令我高兴得很。
“可是‘美女’真的不是很好的名字,”我大声说道,“你不知道小孩都会开这种名字的玩笑吗?”
外婆把一朵小小的蓝色玫瑰放在蛋糕上。
……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这是一本出色的小说,露丝·怀特女士是一位真正懂得抒发情感的作家。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怀特女士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让我们真正的自我发扬光大。
——《学校图书馆学报》(Sehool Libra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