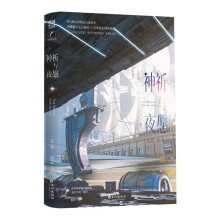他们似乎顺着山坡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但其实或许很短;因为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没有风吹云涌,没有星星的升落。随后他们来到了这里的一座城市的街道上,阿仁看见这里房子的窗户中都没有灯光,那些死人站立在一些门道中,表情平静,两手空空。<br> 所有的市场上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叫买叫卖,没有人花钱没有人挣钱。没有人使用任何东西;没有人制造任何东西。杰德和阿仁两个人孤零零地穿过那些狭窄的街道,尽管有几次他们在路口拐弯的时候看到过人影,但因为光线惨淡,相隔甚远而难以看清。阿仁看到第一个人影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他举起长剑指着人影,但是杰德摇摇头,继续向前走。随后阿仁看见那人影原来是一个行动缓慢的女人,她没有从他们面前逃走。<br> 他们看见的所有人影——不是很多,虽然死人很多,但这个地方很大——都站着一动不动,或者在漫无目的地缓缓移动。他们的身上都没有伤口,这一点与在其死亡之地被召唤到白昼中的艾瑞斯阿克博相似。他们的身上也没有疾病的痕迹。他们完好无损,疾病已被治愈。他们已被治愈了痛苦,结束了生命。他们不像阿仁曾经担心的那样令人恶心,也不像他曾经想象的那样恐怖吓人。他们的表情平静,没有愤怒和欲望,他们那朦胧的眼睛中也没有任何希望。<br> 在罗科岛的大殿堂西边的某个地方,时常是偏南一点,人们经常会看见那座内在林。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除了那些知道去那儿的路的人,没有人知道还有路可以去那儿。但是即便是那些初来乍到的学生,还有那些城里人乡下人,只要站在某个特定的位置,总是能看见它:一片高高的林木,即使在春天,碧绿的树叶也会泛着金光。于是他们——那些初来乍到的学生,那些城里人乡下人——都认为那座树林在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移动。但是,就这一点来说,他们都弄错了,因为树林不会移动。树根是实实在在的树根。移动的是其他的一切。<br> 杰德离开了大殿堂,走在田野上。他脱去了白斗篷,因为正午的太阳当头照着,照得他浑身发热。一位正在褐色的山腰间犁地的农夫举手向他敬礼,杰德举手还礼。小鸟唱着歌儿飞向天空。休耕的田地里以及马路旁的火花草花蕾初绽。远处的天宇中,一只飞鹰划出一道巨大的圆弧。杰德抬头瞟了一眼,再次举起一只手。那只大鸟急冲而下,翅膀带着呼呼的风声,径直落在那只伸在空中的手腕上,黄色的爪子抓得牢牢的。这不是一只雀鹰,而是一只巨大的罗科岛的恩德隼,一只棕白色条纹相间的猎鹰。它歪着脑袋,用一只圆溜溜金灿灿的眼睛看着超级大男巫,然后咂巴着弯钩似的喙,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两只圆溜溜金灿灿的眼睛同时直愣愣地瞪着他。“无畏。”超级大男巫用创世的语言对它说道。<br> 那只巨鹰扑扇着翅膀,脚爪牢牢地抓着超级大男巫的手腕,目不转睛地看着他。<br> “去吧,兄弟,英勇无畏的人。”<br> 在明朗的天空下,远处山腰间那位干活的农夫放下手中的活计看着他们。去年秋天有一次,他也曾看到超级大男巫将一只野鸟放在手腕上,随后片刻之间人就不见了,只有两只巨鹰临风盘旋而上,飞向天宇。<br> 这一次那位农夫却看着他们分手了:那只大鸟飞向高空,那个人却踏着泥泞的田野继续向前走去。<br> 他来到了那条通往那座内在林的小路。不论时光流逝,世界变迁,那条小路总是笔直向前。超级大男巫顺着小路很快走进了林阴之中。<br> 一些树木的树干粗壮无比。亲眼看到它们之后,人们就会相信这座树林绝不会移动:它们像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灰蒙蒙的纪念塔;树根像牢固的山脚。然而在这些最古老的树木中,有些已经树叶稀疏,枝条枯死。它们并非长生不死的灵树。在这些参天巨树当中,生长着一些高大的年轻树木,枝繁叶茂的树冠充满勃勃生机,还有一些长着嫩叶的树苗,细嫩的枝条尚不及女孩儿的个头高。<br> 树下的地面上常年落叶缤纷,腐烂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蕨类植物和一些矮个儿林地植被生长其间,除了这惟一一种在地海的哈迪克语言中叫不上名字的树木外,没有其他任何种类的树木。站在这些枝叶下面,清新的空气中洋溢着一股泥土的气息,嘴巴中好像还有一种潺潺流淌的泉水的味道。<br> 在一块数年前因砍伐了一棵巨树而留下的空地上,杰德见到了定型大师。定型大师深居林木之中,很少或者说从不抛头露面。他的头发是黄油一样的黄色;他一点儿没有生活在群岛上的人的样子。自从艾瑞斯阿克博戒环得以恢复之后,卡尔加德的野蛮人已经停止了他们的突袭行动,和内陆就贸易与和平达成了一些协议。他们并非友好和善之人,总是趾高气扬。但是偶尔会有一个年轻的武士或者商人的儿子,由于热望冒险或者渴望学习巫术,忍受不了诱惑,独自一人西行前来罗科岛。十年前,定型大师,这位来自卡莱果—阿的年轻的野蛮人,就是这样身佩长剑来到罗科岛的。他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来到了罗科,用半生不熟的哈迪克语迫切地告诉看门大师说:“我是来学习的!”现在,一个高大而白皙的男人,金黄色的长发,一双奇特的绿眼睛,站在树下泛着金光的绿色光影中,这就是地海的定型大师。<br> 或许他也知道杰德的名字,但是即便如此,他却从来不叫他的名字。他们无声地互致问候。<br> 只见赭黑色的鳞片闪亮耀眼,一对长长的眼睛发出炫目的光束,红红的舌头有如一条火舌。龙嘶嘶地吼叫着,盘旋着,降落在悬岩上。它喷出一口火焰,空气中顿时充满物体烧焦的异味。<br> 龙爪撞击在岩石上,铿锵有声,多刺的尾巴扭动着,咔咔作响,巨大的龙翼收拢在长有硬甲的两肋,发出狂怒的咆哮和飒飒的风声,阳光照射之下,透出一片猩红。龙缓缓侧过脑袋,看着女人。女人站在长柄镰刀似的龙爪跟前,也在看着龙。她能感觉到龙身上的热气扑面而来。<br> 听说男人绝不可以盯着龙的眼睛看……<br> 中谷的农夫打火石死后,他的遗孀继续住在他的农舍里。寡妇的儿子在船上做水手,女儿嫁给了谷口的一个商人,所以只有寡妇一个人住在橡树农庄。寡妇不是本地人,人们传说在她家乡的那个地方,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事实上,魔法师奥金路过橡树农庄的时候来看过她。可那算不上什么,因为奥金总是拜访各种各样的小人物。<br> 女人有一个外乡名字,不过打火石管她叫哥哈,贡特当地人用这名字来叫一种白色小蜘蛛,这种蜘蛛擅长结网。这名字对她很合适,因为她也长着白白的皮肤,生得小巧玲珑,而且擅长纺织山羊毛和绵羊毛。而眼下她成了打火石的寡妇哥哈,一个主妇,她拥有一群羊和一片可以放羊的牧场,四块可耕种的土地,一个梨树园,两所供佃农住的房子,橡树下那幢古老的石头房子,还有山那边的家庭墓地,打火石就躺在那儿,埋在自家地里。<br> “我总住在墓碑附近,”哥哈对她女儿说。<br> “噢,妈妈,到镇上来和我们一起住吧!”苹果说,但是寡妇不愿意离开自己清静的居所。<br> “也许以后,等你们有了孩子,需要帮手,”她说,愉快地看着灰眼睛的女儿。“但是现在不行。你不需要我,我也喜欢这儿。”<br> 苹果又回到年轻的丈夫身边去了。寡妇关上门,站在农舍厨房的石板地上。天色已晚,她没有点灯,又回想起丈夫以前点灯的情景:那双手,那火星,还有迷人的灯光下他神情专注的黝黑的脸庞。房子里静悄悄的。<br> “我以前自个儿住在一所寂静的房子里,”她想。“我会再过一次这样的日子。”她点着了灯。<br> 炎热的季节刚开始的一个傍晚,寡妇的老朋友云雀从村子里出来,她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行色匆匆。“哥哈,”看见哥哈在大豆地里除草,云雀说:“哥哈,出事了,是件很糟糕的事。你能跟我走一趟吗?”<br> “可以,”寡妇说,“是什么糟糕事呢?”<br> 云雀不断地喘着气。她是个中年妇女,体态笨重、相貌平平,她的名字和长相一点都不相称。不过,她做姑娘时,体态轻盈,还算漂亮,曾经友善地帮助过哥哈,全不在乎村里人如何流言蜚语地谈论打火石带回家来的这位面色苍白的卡基女巫。从那时候起哥哈和云雀就成了好朋友。<br> “有个孩子烧伤了,”她说。<br> “谁家的?”<br> “流浪女人的。”<br> 哥哈去把门锁了,两人一起沿着小路出发,云雀一边走一边说个不停。她气喘吁吁,汗水涔涔。小路两边茂密的杂草长满了细小的种子,草籽粘了她满脸。云雀边说话,边用手抹掉那些草籽。“这些人在河滩的草地上扎营整整有一个月了。一个男人,冒充白铁匠,可他是个贼。有个女人跟他在一起。还有一个男人,年纪轻一点的,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些人谁也不干活,干点小偷小摸啦,乞讨啦,要么就是靠那个女人过日子。河下游的那些小伙子为了接近那个女人,就给他们带些地里出产的东西。你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那种事情。我要是你,这些天就会锁上屋门。后来这个家伙,就是那个年轻一点的男人,来到了村子里,我当时正在屋外。他跟我说:‘孩子不舒服。’我以前几乎从来没见过他们带着孩子——像个小鼬鼠一样的东西,在眼前一闪很快就溜过去了,我都拿不准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于是我说:‘不舒服?是发烧吗?’那个家伙说:‘她点火的时候不小心烧伤了。’我还没准备好跟他一起走,他就跑得不见了踪影。等我来到河边他们待的地方,另外的那对男女也不见了,都走了,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连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破破烂烂的东西都不见了。只剩下营火还在闷烧着,孩子就在地上——在火堆旁——半截身子埋在火堆里——”<br> 云雀沉默了一会儿,脚下仍是不停,眼睛盯着前面,也不看哥哈。<br> “他们连条毯子都没给她盖,”她说。<br> 云雀马不停蹄,继续赶路。<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