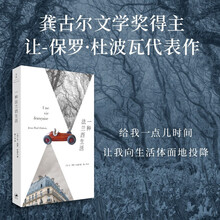我们很快便看到了结果。
那栋粉红色的房子里几乎彻夜喧嚣,许多衣着不整的女人在房里大声喊叫,每当我走过那粉红色房子时,那些女人便用脏话戏弄我,还有些女人嘴里嚼着东西朝我喊:“来找你妈妈玩!”除了那些女人外,还有许多坐着吉普车来的美国大兵,于是,狂笑和尖叫声充斥着整条米格尔街。
海特说:“要知道,乔治这家伙败坏了咱们这条街的名声。”
米格尔街几乎成了这些新来者们的天下,海特和其他人坐在路旁聊天,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被打破了。
可是,博加特倒对这些新来的人挺友好,每周有两三个夜晚和她们搅在一起。他装出一副对这一切很厌恶的样子,可我根本不相信,他总是口是心非。
“多利怎么样呀?”一天海特问他。
“她还成。”博加特应了一句,意思是说她挺好。
“噢,她还成,”海特说,“说说看,她倒是怎么个成法?”
“嗯,她打扫房间,做饭。”
“侍候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从博加特的话语得知,伊莱亚斯有自己的房间,一回家便呆在里面不出来。他在外面吃饭,他正在学习,准备参加一次重要的考试,对家里发生的一切毫不感兴趣。
乔治照样拼命喝酒,生意却十分兴旺,他穿起西装,还扎上了领带。
海特说:“如果他能好好地贿赂警察和那些人的话,肯定能挣大钱。”
我简直弄不明白,那些新来的女人为什么那么听他的话,似乎挺喜欢也挺敬重他,乔治却仍是老样子,一点也不像善待她们的样子。
一天,他对大伙说:“多利现在没有妈妈,我是又当爹又当娘,我看她已经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他挑选了一个叫雷泽(原意为剃刀)的男人当女婿,再也没有比这个名字更合适他的了。他又矮又瘦,棱角分明,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撮修得整整齐齐尖尖的小胡子,他的裤缝总是熨得笔挺,身板挺得溜直,就像腰里别着一把刀似的。
而多利照旧不停地格格傻笑。
雷泽和多利从教堂结完婚,回到粉红色的房子里举行招待会,那些女人也都穿戴打扮起来,还来了不少美国大兵和水兵,喝酒、狂欢,向乔治祝贺。那些女人和美国佬逼着多利和雷泽不停地亲嘴,他们哄闹着,多利格格地傻笑着。
海特说:“知道吗?她那不是笑而在哭呢。”
那天,伊莱亚斯没在家。
女人和美国佬们唱起《甜蜜的十六岁》和《光阴流逝》,然后又起哄让多利和雷泽亲嘴,忽而有人喊道: “让他们讲话!”大伙哄笑着喊起来,“讲话!讲话呀!”
雷泽一言不发,只剩多利一人在傻笑。
“讲话,讲话啊!”客人们齐声喊叫着。
多利越发格格地傻笑。
最后,乔治开腔了:“多利,不错,你是结婚了,可别认为你就可以骑在我头上,翘尾巴了。”这些诙谐的话引起客人们一阵哄堂大笑。
多利停止傻笑,呆呆地望着大伙。
一阵极为短暂的沉默,死一般的沉静,忽然,一个美国水兵挥起手,醉醺醺地喊道:“你可以让这姑娘干点好活儿吗,乔治。”众人大笑起来。
多利从院里抓起一把沙土,举手正要朝水兵扬过去,却忽然停住,大哭起来。
顿时,爆发出一阵狂呼,欢笑。
我不知多利后来怎么样了。一天,爱德华说她住在桑哥格瑞德,海特说看见她在乔治大街市场上卖东西。总之,她离开了米格尔街再也没有回来过。
过了几个月,来的女人越来越少,停在乔治家门前的吉普车也少多了。
“你们看见了吧?”海特说。
博加特点点头。
海特补充说:“如今在西班牙港,他们有许多好地方可去。乔治的毛病在于他太蠢,根本不配当一个大老板。”
海特不愧是个预言家,过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那栋粉红色房子里就剩乔治孤零零一个人了。我常看见他一人坐在门前水泥台阶上,他再也不注意我了。他萎靡不振,神色凄惨,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不久,他死了。海特和那些哥儿们凑了点钱把他埋葬在拉如斯墓地,伊莱亚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