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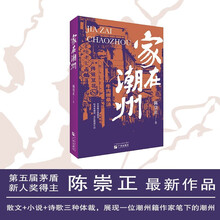
第一章 邂逅亨丽埃特
我叫科尔内留斯,这是我父亲的过错。很多故事里。一开头肯定总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而我读的故事里面,却总有一些十分著名的人物。这也是我父亲的过错。
我在学校里叫科尼,母亲也这样叫我。我和母亲住在一栋相当陈旧的房子里,她一间,我一间,还有一个房间是给卡利德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但大多数时间,那里没有人住。母亲夜里工作,白天睡觉。我每天放学回来,她总是坐在电视机前喝葡萄酒,有时还在玩儿拼图游戏,这要耗费很多时间。但是到了最后总是缺少一块,她经常为这个烦恼。我感觉得到,母亲不得不这么辛苦地干活,因为一切都要花钱,她也常常为这个烦恼。我觉得她很悲伤,我也很悲伤,我们谁也帮不了谁,尽管我们肯定都很愿意帮助对方。
我家住在柏林市中心区的边缘,差不多快到科罗伊茨贝格区那边了。如果我说“那边”,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到科罗伊茨贝格区的儿童农庄玩耍,骑小马,攀障碍和喂小兔子时,就好像是来到了火星人当中,显得特别紧张。其实那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我们学校里有些人,虽然根本就没有去过科罗伊茨贝格,但我也不怎么喜欢他们。
唯一叫我科尔内留斯的人,就是杜德克先生。自从住在离我们三栋房子以外的克拉夫特夫人死了以后,杜德克先生就成了我的钢琴老师。杜德克先生还不太老,可是一到我们要在班上表演的时候,他就变得格外严格,有时也很滑稽。这时他会穿上笔挺的西装,戴上领结,然后发表一场演说。在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他都会告诉我们,这是个什么样的曲子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他说的真是“研究”两个字。每当我进入课堂时,杜德克先生大多是坐在三角钢琴上,嘴里嚼着面包夹香肠,很少提什么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什么是完美。我告诉他,完美就是和谐。杜德克先生立即从钢琴上跳下,把我的回答记录了下来。在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父亲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和我母亲结婚。母亲说,他把搬过来时带来的东西,全部留了下来。其实仅仅是一只小柜子,现在就摆放在我的房间里。可以想象,我的父亲是一个名人,因为他柜子里的书都是有关名人的。而我的名气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相当曲折的故事。
一天夜里,我干脆离家出走了。我家前面的街道很暗,而且出奇地安静。再往前走一段,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朝着一家农户的方向走去,老是踩到水洼里。我边走边想,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往前走,我的鞋都湿透了,况且也不知道到底要到哪儿去。忽然,我发现前面的街道比这里亮堂,有很多人在走路。这我都能够看见,但就是听不到声音。这里寂静得出奇,就好像是不出声的电视画面。没有声音,我觉得很恐怖。感谢上帝,我终于可以听到一切了,其实只要走到近前就可以听到,所以我才继续往前走去。
到了阿达贝大街,我已经闻到了克巴烤肉的香味。走到下一个街角,只见几个男人坐在便道上喝着罐装啤酒。我走过的时候,一个男子把空易拉罐抛向空中。易拉罐翻了几个跟头又落回到他的手上。
“空啦,空啦,都空啦!”那个男子说,“东西一空,就变得轻灵了,就可以飞了,就可以翻跟头了,就是从中什么都得不到了,真可惜。”
他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你是一个小孩儿,”他说,“你不懂。回家喝你的芬达去吧!”
我没有回家,而是向左拐,顺着大街走下去,一直到了一个广场上,那里有一座喷泉,周围摆满了长凳。长凳之间种着大树和灌木丛,它们很浓密,人可以藏到里面。我坐下,盯着喷泉上那些滑稽的雕像,上面到处是喷射着水花的小孔,水最后都聚集在一个大圆盆里。水面上漂浮着落叶和垃圾。路灯暗淡地照着广场。喷泉上的雕像把影子抛向了地面,看起来就好像即将上演一场恐怖电影。我想象着他们都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是鬼怪的声音吗?鬼怪的声音可能是低沉的、嗷嗷叫的、不清晰的,那就要看他们是扮演好鬼还是坏的鬼怪了。他们可能会说:“嗨,你过来,我要把你吃掉。”嘴里还啧啧作响,或者他们会说:“嘿,不要跑掉,我并不像长的那样可怕。”
“我并不像长的那样可怕。”
真的有人说了这句话吗?我突然害怕了,尽管我并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我抬眼向上望去,其中的一个鬼怪身影动了起来,然后就有一个人坐到了我的身边。我不敢把脸转过去,但我身边的影子很平和。这至少使我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
“其实没有什么,”那个影子说,“其实也不那么可怕。在夜里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我一直坐在喷泉边儿上,我在想,或许可以到你的身边来。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是不是?即使我老了,很胖也很丑,我或许是个中了魔法的公主。可能还是不可能?有人可能是中了魔法的巫婆,但却很美,你看不出她是个巫婆。如果是一个中了魔法的公主,那就更没有人能够把她认出来了。”
“那倒是。”我对那个鬼怪影子说。我已经不害怕了,然后把头转了过去。在我身边坐着一个女人,她真的很胖,肯定比我母亲还胖。我母亲老是想减肥,却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其实我倒是无所谓。我想仔细看看身边这个人,但在阴暗中却不能一下子看清。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了她的面庞。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很面熟。这张面孔很友善,不让人害怕,但总是觉得有一丝忧伤,但愿有人能够明白我说的意思。我很喜欢这张面孔。
“你可以叫我亨丽埃特,”我的新相识说,“我有很多名字,但现在我就是亨丽埃特。这听起来比较高贵典雅,对我正好合适。”
“我觉得也是,”我说,“亨丽埃特和科尔内留斯。”
亨丽埃特吃惊地看着我,然后笑了起来。她的双下巴高兴得直颤,我可以保证,连她的耳朵都在动。我也笑了,我们又在一起坐了一会儿,仍然很兴奋。
“为了这个,我们必须去喝一杯。”亨丽埃特突然说,“尽管我们已经以‘你’相称,而且我现在才知道你叫什么,但我总觉得,我好像已经认识你很久很久了。这种事情是有的,对不对?名字就如星相一样,总有两个特别相配。”
亨丽埃特站了起来,让月光照在她身上。斜斜的光线把她变成了一只怪物,就像是恐龙什么的。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个人。我在思考,亨丽埃特这个人,我好像不应该就这么跟她走。
“我们去绿琴酒店。”亨丽埃特说。
绿琴酒店,听起来还不错。其实,亨丽埃特也不一定想绑架我,从我母亲那儿反正是敲诈不来赎金的。我干脆跟在她的身后,绕过喷泉,穿过树丛。亨丽埃特的衣服老是被树枝挂住,每次都得用一刻钟的时间才能使她摆脱出来。
“这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我说,“就像是莱温斯顿在非洲。”
莱温斯顿是我房间书柜里一本书中的名人,这个人老是喜欢去没有人烟的地方。
“你在这里很容易迷路的,”亨丽埃特再一次摆脱树丛后对我说,“特别是你不认识什么人的时候,对不对?这真是让人发疯,我的宝贝儿。如果你知道有人喜欢你,可那个人却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那你不论在哪儿,都会感到生活是那么美好。他会找到你的,但有可能他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终于穿过了树丛,她把大衣上的树叶抖掉。我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但我喜欢听她的声音。我们跑过一片草地,听到了喧闹声,这是各种声音很舒服的混合。它们来自那个小酒馆,就是亨丽埃特邀请我去的地方。
我和母亲也去过小酒馆,但从来没有这么晚去过。因为我们一般吃过饭后才去,只待母亲把五个马克都输给赌博机之后就离开,而且那通常是很快的。下午去的话,那里的人也不多,而且几乎没有人喝醉。
绿琴酒店的大门上悬挂着绿色小提琴模样的广告灯,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那东西也不太像,小提琴上只能安三根弦和两条弦轴。进门以后,我先得习惯里面障眼的雾气和朦胧的光线。然后,我见到左边是一个吧台,右边是几张桌子和一条通往后面房间的走廊。酒店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都显得很疲惫,不像有人刚刚做过鲜活细胞疗法的样子。我曾在报上读到过,赫伯特?冯?卡拉扬,为了显得年轻一些,每年都要接受一次这样的治疗,但他最终还是死了。
大多数人好像都认识亨丽埃特。我们还站在门口时,吧台后面的那个女人已经给她送过来一杯啤酒了。
“小家伙想要什么?”她看了一眼亨丽埃特,亨丽埃特看了我一眼。
“可乐,”我说,“多放些冰块。”
“给小宝贝儿一杯多放冰的可乐。”亨丽埃特说。
“OK,”女招待说,“加冰的可乐。你们坐到后面去吧,那里对孩子很合适。”
……
——奥登堡少儿图书奖评语
人生总会遇上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这往往是成长的契机。
——《书评》(Book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