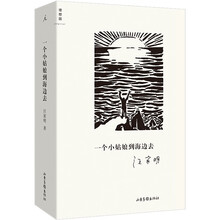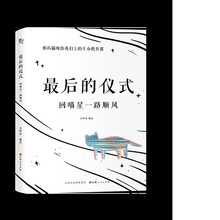大陆上的茶很清淡,可是用的是贵重的瓷茶具;而在此地,人们从破损
的铁壶里漫不经心地倒出玉液琼浆给顾客做提神饮料,价格极便宜,而且是
倒在陶制的杯子里。
早餐很可口,茶也不负盛名。此外,倒茶的年轻爱尔兰女郎还无偿地馈
赠着微笑。
我浏览着杂志,首先读到一则读者来信,信中要求把高高在上的纳尔逊
推倒,而代之以圣母雕像。又有一则来信,要求推倒纳尔逊,还有一则……
已经8点了,交谈的情绪勃发,我也被卷入其中:我被谈话的声音淹没
了,但我从中只听懂了唯一的一个词:德国。我决定运用一下这个国家的武
器,当然肯定是很友好的,即用对不起回敬大方的女茶神无偿的微笑,直到
猛然爆发的宛若轰雷的一声吼把我吓了一跳为止。难道在这个奇特的岛国,
铁路交通竞如此繁忙吗?吼声停了,声音转为清亮,最后的晚餐的激昂序曲
从备餐直到敬谢圣餐仪式都能清晰而纯正地听到,一直到最后一个音节唱完
的声音从对面圣安德列斯教堂越过韦斯特兰大街传来。于是,我在这里第一
次喝的几杯茶同以后我将在空旷而肮脏的小镇上、旅馆里以及壁炉边喝的许
许多多杯茶都很好;于是,给我留下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虔诚的印象,就像这
种虔诚不久前在最后的晚餐之后淹没了韦斯特兰大街那样。这么多的人从教
堂走出来,在我们那儿只有在复活节的弥撒或者圣诞节的礼拜仪式之后才能
看到;但是,身影分明的不信上帝者的忏悔我却不曾忘怀。
刚刚早晨8点钟,又是星期天,此刻把主人从梦中扰醒还太早。不过茶
已经凉了,咖啡店里扑出了羊油的气味,旅客收拾起纸盒和箱子朝公共汽车
站拥去。我兴味索然地翻阅着《爱尔兰文摘》,结结巴巴地译读着一些文章
和小故事的开头部分,直到第23页上的一则至理名言引起我的注意——在我
能把它译成德文之前,我琢磨了良久;不经翻译,不是用德文来理解,然而
我却懂了,几乎比译成德文表达得还明白——坟墓中躺满了人,若没有他们
世界便不能生存。
读过这句至理名言之后,我觉得来都柏林旅行是很值得的。于是,我决
定:为了我将来会感到的重要时刻,把它深深锁在我的心底(后来,它看来
对我是一把钥匙,可用以解释我将经常碰到的、由激昂和镇静组成的这一奇
特的混合,那种使人发狂的疲惫,以狂热劲头连结着的冷漠)。
当我下决心不再顾忌过早搅醒东道主的鲁莽以后,我来到那隐藏在杜鹃
花丛、棕榈树和夹竹桃丛后面的阴凉的巨大别墅前;远处的山峦和丛林依稀
可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