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现在言归正传,也就是说在我还爬树的时代,——不瞒你说,我爬得次数多、技术好,而且也并非老从树上掉下来!——就连那种下面寸枝不生、周身光秃秃的树干也不在话下。我甚至可以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上,在树上修建瞭望台,造了数不清的树屋,其中还有一座很像样的位于森林中央,离地十米高,有顶有窗还有地毯垫底。呵,说来你也许不信,我童年时代的大部分光阴就是在树上度过的:我吃在树上,读在树上,写在树上,睡在树上,在树上学英语单词和拉丁语的不规则动词,也学数学公式和诸如前面提到过的伽利略落体定律的物理规则,总而言之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在树上,包括口头和笔头的家庭作业。最开心的莫过于从树上往下撒尿了,那射出的尿液在豌豆中划出一道高高的弧形,穿过浓密的阔叶、针叶稀里哗啦地纷然落下。
树上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妈妈那讨厌的呼唤和哥哥颐指气使的命令都传不上来,唯有清风拂过,树叶低语,树干轻柔地晃动声……从树上放眼四望则令人心旷神怡:我的目光不仅可以越过自己的家院,还越过别人的家院,甚至越过那座湖泊和湖泊后面的平原,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峦。当傍晚夕阳西下,站在地上的人早已看不见那沉入山后的一轮残阳时,我却还能在自己的树顶上欣赏它的余辉,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在空中飞翔,虽然也许没那么刺激、没那么潇洒,但至少也是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享受吧。更何况本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身高已一米十八,体重亦达二十三公斤,对飞行来说我已明显的超重了。即便是来上一场货真价实的风暴,我解开上衣并大敞开衣襟也无济于事。不过我想,至于上树吗,那是可以活到老爬到老的。就是到了一百二十岁,我已成了一个耳聋眼花、手抖腿颤的糟老头子,仍然还可以像个老猴子似的高坐在那榆树、榉树和枞树的顶端,让微风轻摇,放眼大地,将湖泊和山后的景色尽收眼底……
天晓得我怎么会在这儿大谈什么飞翔啦、爬树啦的鬼事l唠叨什么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和让我神志紊乱的后脑勺晴雨表效应!而我本来要讲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只要能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关于夏先生的故事,因为其实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故事可言,而只是有这么个怪人,他的人生之路——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他的漫游之路,有几次竟与我不期而遇。不过我最好还是从头说起吧。
在我还爬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或者确切点说不是在我们下湖村,而是在邻近的上湖村,不过这也无法分得那么清楚,因为上湖、下湖以及其他村子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村与村都是沿湖相连,无明显的首尾之分。恰似一条由花园、房舍、场院和小船库组成的细链……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离我们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那么个叫“夏先生”的人。谁也不知道夏先生叫夏什么,是彼得还是保罗,是海因里希还是弗兰茨—克萨维尔。也许应该称呼他夏博士或者夏教授或者夏教授兼博士。总之,人们只知道他叫“夏先生”。也没有人知道夏先生那时是否有份工作,究竟有没有过工作或者曾经一度有过工作。人们只晓得夏太太有工作,是个做布娃娃的。日复一日,她天天坐在油漆匠施坦格迈尔宅第里那半截嵌入地下的家中,用羊毛、布料和锯木屑制作小孩玩的布娃娃,并每周一次把产品打成一个大邮包送到邮局寄出去。在离开邮局回家的路上,夏太太要挨个光顾杂货店、面包房、肉铺和菜摊,然后拎着四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回到家中,在此后的一星期里,她便足不出户,闭门造车。谁也不清楚夏家两口子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来了,女的坐车,男的走路,打那以后这地方就有了他们。夫妇俩没儿没女,无亲无眷,也从未有过客人造访。
“‘幽闭恐怖症’一词源厂拉丁希腊语,”父亲接着说,“这点想必卢赫特汉德大夫肯定清楚。它是由‘claustrum’和‘phobia’两部分组成的。而拉丁希腊语里的‘幽闭’与德语的‘关闭’或‘封闭’近义,这一意思在德语的‘隐居幽室’一词中或者克劳森市的市名上以及意大利语‘Chiusa’里也有体现,在法语里则与Vaudusee一词对应。你们谁还能举出一个带有‘claustrum’含义的词来吗?”
“我!”姐姐叫道,“我听丽塔·施坦格尔迈尔说,夏先生总爱打哆嗦,而且是浑身上下抖个不停。丽塔说,他患有一种类似幼儿多动症的肌肉抽搐病。只要他屁股一粘凳子,人就开始颤抖。只有当他迈开双腿时,才不发抖,所以他不得不总是人在途中,好不让人看见他打哆嗦的样子。”
“在这一点上,他就像个刚满周岁的孩子。”父亲说,“或者说如同一匹两岁的幼马,第一次参赛时站在起跑线上也会同样抽搐、发抖,紧张得全身哆嗦个不停,搞得骑手们手忙脚乱地拼命勒住缰绳。不过以后就自然习惯了,要么就是给马戴上眼罩。你们谁知道,‘勒紧缰绳’是什么意思?”
“胡说八道!”母亲嚷道,“要是让夏先生坐进你们的车,他肯定也会抖起来的。稍微有点颤抖,这又碍着谁的事了!”
“恐怕,”父亲自以为是,“夏先生是因为我讲了句俗语才没上我们的车——我说:‘您这样会得病见阎王的!’我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冒山这么一句话来。我敢说,要是自己用的是=句没这么俗气的表达的话,夏先生肯定就上车了,比方说……”
“瞎说,”母亲断然否定,“他不上车是因为他有幽闭恐怖症,所以他不但不能待在屋子里,而且也无法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汽车内。不信你问问卢赫特汉德大夫!只要夏先生待在封闭的空间里,不管是房内还是车内,他就会冒火。”
“冒什么火?”我问。
“也许,”比我大五岁的哥哥说,他已经通读了所有的格林童话,“也许夏先生和童话故事《六好汉闯天下》里的飞毛腿一样,一天工夫能绕地球跑一圈。每次回到家里,他都得用皮条把自己的腿吊起来,否则他的脚就停不下来。”
“这当然也是一种办法。”父亲肯定道,“没准夏先生就是多长了一条腿,所以总要跑路。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卢赫特汉德大夫把他的一条腿给吊起来。”
“瞎说!”母亲显然不同意,“夏先生只得了幽闭恐怖症,没有别的毛病。而这幽闭恐怖症是无药可治的。”
我上床后,脑袋里还老是转悠着“幽闭恐怖症”这个怪词,并且自言自语地反复念道了好几遍,以免以后把它搞忘:“幽闭恐怖症……幽闭恐怖症……夏先生得了幽闭恐怖症……也就是说,他无法待在室内……他无法待在室内就是说他总要在外面乱跑……因为他得了幽闭恐怖症,所以总要在外面乱跑……不过如果说‘幽闭恐怖症’就等于‘无法——待在——室内’,而‘无法——待在——室内’就等于‘总要——在外面——乱跑’的话,那么‘总要——在外面——乱跑’也就等于‘幽闭恐怖症’……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总要——在外面——乱跑’来代替‘幽闭恐怖症’这个晦涩拗口的单词……这就意味着,假如母亲说:‘夏先生总要在外面乱跑,是因为他有幽闭恐怖症’,就好比她是在讲:‘夏先生总要在外面乱跑,是因为他总要在外面乱跑’……”
想到这儿我的头有点发晕了,便试着赶快忘掉这发疯的新词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同时反过来想象:夏先生什么事也没有、什么病也没得,而只是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就跟我乐意爬树一样。在外奔波是他自己的一大乐趣和一种享受,仅此而已,别无他因。而晚餐饭桌上大人们臆想出来的一切混乱的解释和拉丁词语,全都和那个《六好汉闯天下》里的把腿吊起来的故事一样,纯属瞎编。
然而才过了一会儿我就又想起了透过汽车后窗看到的夏先生的那张脸,仿佛又看见了他雨水横流的脸上那半开半合的嘴和瞪得贼大的呈惊恐状的双眼,于是心里暗暗嘀咕:谁会在开心时用这种目光看世界;没有哪个在做自己喜欢、乐意做的事情时会是这样一副表情的。这副模样只有内心充满了恐惧的人才具备。或者是谁口渴了,而且是在雨中渴得好像能喝干一座湖时才会有这样一副嘴脸。想到这儿,我的脑袋不由得又是一阵眩晕。我竭尽全力试图忘掉夏先生那张脸,可是越想忘掉,它就越是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每一道褶子,每一条皱纹,都历历在目;每一颗汗珠,每一滴雨水,全分明可见;还有那微微颤动的嘴唇,好像在嗫嚅什么。这声音似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响亮,最后我终于听清了夏先生恳切的请求:“求你们闭闭嘴,别再打搅我行不行!求你们闭闭嘴,别再打搅我行不行、行不行……”
只是到了此刻,我才得以摆脱对夏先生的胡思乱想,他的声音帮了我的大忙。于是,那张脸消失了,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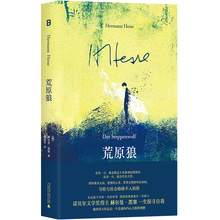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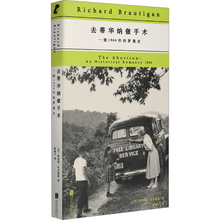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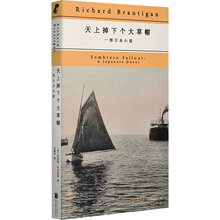

一段并不轻松的
童年回忆
童年,总是和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等美丽动听的词句联系在一起,有关童年的回忆自然也往往充满了孩提时代那色彩斑斓、童趣盎然的画面,使人心潮激荡,让人浮想联翩。然而,德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在小说《夏先生的故事》里展示的一段主人公的童年回忆,却让那富有诗情画意、略带怀旧伤感的宁里行间多了分作者对人上世界深沉的思考和独特的理解。
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一部《香水》一下香遍了全球并流芳至今的聚斯金德,在1991年推出了《夏先生的故事》这本小书,当时距其上一部作品《鸽子》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四年。沉寂了如此长时间的他,一反其以往奇幻怪异的创作方式,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向人们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情节简单、内容平凡而且年代并不久远的当代童话。书中的“我”是一个住在农村的毛头少年,粗泛读来,使人觉得仿佛他是作品的主角,—切故事情节均围绕其遭遇展开。“我”从小就爱爬树,喜欢在树上学习、嬉戏,几乎到了以树为友、以树为家的地步因为树上超尘拔俗,远离世间的喧嚣和人生的烦恼,让人神清气爽,身心舒畅。就连决定“告别人世”的地点时,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自己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参天大树。此外,朦胧的恋,学车的故事,练琴的经历,纯真无邪的心理,喜怒哀乐的童趣,通过作者生动形象的描写,跃然纸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倘若没有夏先生的出现,这本书会成为一篇追思儿时往事的精致小品。而恰恰因为有了这位容易被人忽视却又的确叫“我”终生难忘的“怪客”,使人感受到这部作品思想内涵的分量,领悟到作者的匠心所在。夏先生同“我”的几次不期而遇,恰似—条红线贯穿全书,给作品的主题定下了基凋。虽然作者对这个“幽闭恐怖症”的患者未作浓墨重彩地描绘,但寥寥数笔点睛的刻画,则把一个性格古怪、行为离奇的“独行者”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冬大,他身披一件又长又宽且特别僵硬的黑色大氅,脚蹬一双胶皮靴,光头上扣着个红色的带穗线帽;而夏人——一年四季中夏天对夏先生来说是最长的季节,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特意给他安了一个“夏”的姓名——夏先生则戴一顶缠着黑布带的扁草帽,穿一件酱色的衬衫和一条相同颜色的短裤。有两件东西是和他春夏秋冬形影不离的,其一是拐杖,其二是背囊。对夏先生的身世,作者没作详细的交代;而对其外貌的描写也仅限于“短裤下和登山靴上光裸着的一节爬满青筋的白腿”以及一双“睁得贼大且呈惊恐状的眼睛”。书中的夏先生由于“患病”,不得不满世界乱跑,不和在疲倦地奔波,既无明确的目的,也没特别的需求。最后,如同当初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样,他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