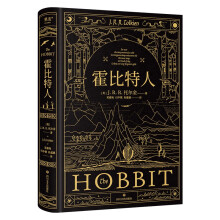于是我乘船出门求学去了,以便能考上喀山大学,至少得这样。
上大学的想法是尼·叶甫列英诺夫向我灌输的,他是一个个头小小的年轻人,一个长着一双女人般和蔼可亲眼睛的漂亮小伙子。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屋子的阁楼间。他常见我手里捧着书,这使他很感兴趣,我们就认识了。不久叶甫列英诺夫开始不断地说服我相信自己“绝对是个做学问的料”。
“您天生就是要献身科学的,”他说道,一边漂亮地抖动着他那一头浓密的长发。
我那时还不知道,对科学还可以像一只兔子那样把身体献出去,而叶甫列英诺夫又是那样振振有词地向我证明:各所大学需要的正是像我这样的青年人。看样子,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灵魂感到惊惶不安了。叶甫列英诺夫说,我在喀山可以住在他家里,利用秋冬两季学完中学课程,通过“某些科目”的考试他正是这样说的:“某些科目”——大学里会给我发放公费助学金,再过四五年我就成为一名“学者”了。就是这么回事,非常简单,因为叶甫列英诺夫才十九岁,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自己通过了几门课的考试,就乘船走了,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我也跟随着他的行踪离家远行了。
外婆在替我送行时规劝我说:
“你别对人发脾气,你老要发脾气,变得不近人情、自以为是了!这脾气你是从外公那儿学来的,可你外公他怎么样了呢?他活了那么大岁数,活成了一个傻瓜蛋,这个可怜的老头。你可要记住这一点:不是上帝来审判人,这种事魔鬼才乐意做呢!好啦,再见吧……”
她一边从松弛的古铜色面颊上擦去不轻易掉落的眼泪,一边说:
“咱们再也不会见面啦,这趟出门你要走很远的路,你这坐不住的人,我可快死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疏远了,甚至难得见她一面,现在我突然痛心地感到,如此密切、如此贴心地和我亲近的人我将再也不会与她重逢了。
我站在船尾,看着她站在码头的护栏边用一只手在画十字,另一只手拿着很旧的披肩的一角在擦自己的脸和那双深色的眼睛,眼睛里闪烁的泪花饱含着对人们无可遏制的爱。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座半鞑靼化的城市,一间平屋内拥挤的公寓里。这问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座小山丘上,一条狭窄、寒酸的街道的尽头;房子的一面墙向着一个火灾遗存的废墟,废墟上杂草丛生,在艾蒿、刺实植物和团酸模的草丛问,接骨木的树蓬间,高高耸立着一幢砖房的断垣残壁,断垣残壁的地下则是一个宽广的地窖:一群无家可归的野狗在那里自生自灭。这座地窖留给我极其难忘的印象,它是我上过的大学之一。
叶甫列英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发放给赤贫者的救济金勉强维生。在开头几天我看见这位灰头土脸的寡妇从集市上回来,将买回的食品往厨房的桌子上一放,便解起了一道难解的习题:如何把一小块劣质肉做成够三个健康的小伙子饱餐一顿的美食?而她自己的一份还没有计算在内呢。
她沉默寡言;她灰色的眼睛里凝聚着一匹操劳过度而耗尽精力的马所具有的那种无望、温顺的顽强精神——这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向高山上走去,明知自己走不出困境,却依然拉着它走!
在我到达这儿大约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当时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正在帮她洗菜,她轻轻地、小心翼翼地问我:
“您到这儿来干吗?”
“读书,准备升大学。”
她的双眉连同额头上的黄皮肤徐徐向上挺去,菜刀割伤了她的一根手指,她一面吮吸着鲜血一面坐到椅子上,但立刻又霍地一下站起来说:
“噢,见鬼……”
她用手帕包扎好割伤的手指,夸奖我说:
“您土豆皮削得挺拿手的。”
怎么不会削呢!于是我告诉她我在轮船上打工的经历。她问我:
“您认为要上大学,有这点就够了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