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受最先接触到的人和自然的熏陶而形成性格的时期;弗拉基米尔·萨宁却离开家人,在外面度过了这段时光。任何人都没有照料过他,哪一只手也没有管教过他,这人的心灵便自由而独特地成长起来,像野地里一棵树似的。他多年没有回家了,刚一回来,母亲和利达妹妹几乎都认不得他了:他的面貌、声音、姿态变化不大,可是在他身上却显出一种精神上已趋成熟的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脸上也焕发出一种新的神采。他傍晚坐车到家,走进屋来竟那么平静,仿佛五分钟前刚从这个房间出去似的。他身材高大,头发是浅色的,肩宽背阔,脸上表情平静,只是两边嘴角微带嘲笑意味,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倦意或激动,以致母亲和利达迎接他归来的那股吵吵嚷嚷的兴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他吃饭和喝茶的时候,妹妹坐在他的对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喜爱哥哥,只有那些狂热的年轻姑娘对离家的兄弟才会这样喜爱。利达总是把哥哥想象成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是这所谓与众不同,却是她仿照书本上的描写自己创造出来的。她想把他的生活看做一个不为人理解的伟大人物的悲壮的斗争、磨难与孤寂。“你干什么这样望着我?”萨宁微笑着问她。这种殷勤的微笑,配上出神的平静的目光,就是他脸上常见的表情了。这种微笑本来是既漂亮又招人喜欢的,而奇怪的是利达反而马上就不高兴了。她觉得这种微笑是自满的表现,一点也没有受苦受难与经历斗争的痕迹。利达一言不发,沉思默想着,转移视线,心不在焉地翻起一本书来。午饭吃完了,母亲亲切而温柔地摸了摸萨宁的头,并且说:“现在讲一讲你在那边怎样生活?做过什么事吧?”“做过什么事情?”萨宁微笑着反问,“讲就讲……无非是喝呀,吃呀,睡呀,有时工作,有时什么都不干……”起初以为他不想讲自己的事,可是母亲详细问起时,他却很有兴致地讲了起来。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觉得无论人家对他的讲述抱什么态度,他都无所谓。他温和而殷勤,可是他的态度却缺乏亲人之间那种非同一般的骨肉之情,好像这种温和与殷勤只不过是出自他内心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罢了,犹如蜡烛发光,对一切都给予同样的光亮。他们走到通往花园的凉台上,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利达坐在低处,独自默默地倾听哥哥讲话。一股几乎觉察不出的凉意钻进了她的心里。她以一种年轻女性特有的敏感本能感到哥哥完全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她就像见到陌生人那样腼腆害羞了。黄昏已到,轻柔的夜幕降落在周围。萨宁吸着烟卷,轻淡的烟味同花园里夏天的馨香气息融合在一起了。萨宁讲到生活怎么使他颠沛流离,他怎么不得不多次忍饥受饿,到处流浪,他怎么昌险参加了政治斗争,而当这个事业使他厌烦时,他又怎么抛弃了它。当这所房子隐没在绿阴中的时候,利达和萨宁的四周便有一些凝然不语的好像有生命似的沉思的老树突现出来,这时萨宁突然搂住利达的腰肢,并且用一种不知是亲热还是凶狠的古怪声音说:“你长成个美人儿啦!;……你头一次爱上的那个男子将会是幸福的……”一股热流从他那肌肉发达、铁一般坚强有力的手臂传遍了利达柔软而娇弱的身子。她仿佛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野兽在向她逼近,感到有些难为情,身子哆嗦了一下,急忙躲开了。他们已经走到了河边,这里弥漫着潮气与水气,尖头的苔草沉思地点着头,对岸是一片逐渐远去的变暗的田野、蔚蓝而温暖的天空与最初出现的星星的白光。萨宁离开了利达,不知为什么用两手抓住一条粗树枝,咔嚓一声把它撅成两段,扔进水里去了。一圈圈平稳的水波起伏着,向四方扩散开,岸边的苔草就急忙弯身点头,仿佛在向萨宁致意,像欢迎自家人那样。六点钟左右,阳光灿烂,花园里却已经又有了浅绿色的阴影。空气中充满光亮、寂静与温暖。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在熬果酱,绿油油的椴树下散发出一股股沸沸扬扬的砂糖与马林果又香又浓的味道。萨宁从大清早起就在花坛旁忙着,设法把那些被炎热与灰尘压倒的花枝扶起来。“你最好先拔掉杂草。”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透过袅袅升腾的淡蓝色的炉烟望着他,劝他说:“你吩咐格鲁尼卡一声,她就会给你办好了……”萨宁抬起了满是汗水的愉快的面孔。“干什么呀,”他甩开那贴在额头的头发说,“让它随便生长去吧,任何绿色的东西我都喜爱。”“你真是个怪人!”母亲慈祥地耸了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说,可是不知怎么她对他讲的那句话却很高兴。“你们自己才是怪人呢!”萨宁用充满自信的声调回答,然后走进屋里去洗了手,回来便舒展而平静地坐在桌旁一张藤圈椅上了。他感觉良好,轻松而又快活。绿阴,太阳,蓝天闪着明朗的亮光,涌入了他的心头,使他整个心中都充满幸福之感,他的心也向它们袒露开来了。那些大城市,连同城市里急促的喧嚣与忙乱紧张的生活,都使他反感透了。现在周围是一片阳光与自由,而前途并未使他感到忧虑,因为他准备从生活中获得它所能提供给他的一切。萨宁眯缝起眼来,又伸了个懒腰,非常快活地把自己强健有力的肌肉伸直又绷紧起来。一股平和而轻微的凉风吹来,于是好像整座花园都在作短促的深呼吸似的。一群麻雀在吱喳乱叫,时近时远,狡狯而匆忙地交谈它们那种渺小的、非常重要的却又不为人所理解的生活,而杂色的猎狐狗米尔伸出红舌头,竖起一只耳朵,蹲在新鲜的绿草丛中宽厚地倾听着鸟雀的啼鸣。树叶在头顶上低声簌簌作响,叶子的圆影在平坦的黄沙路面上无声地颤动着。儿子的平静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大动肝火。她喜爱自己所有的孩子,同样也很喜爱他,但是正因为喜爱,她才心情激动,想要惹恼他,刺伤他的自尊心,侮辱他,——只要她的话与她对生活的见解受到重视就行了。她在自己漫长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像那埋在沙土中的蚂蚁一般,不停地营造家庭幸福的脆弱易碎的大厦。这是一长溜好似兵营或医院那样沉闷而单调的建筑物,由一些最小的砖头砌成,她像个平庸的建筑师,把这些砖头看成是生活的装饰物,其实它们有时给她增添麻烦,有时惹她生火,有时使她害怕,而且经常使她忧愁。可是她仍然以为不能不这样生活。“哎,好吧……以后还会这样么?”她瘪着嘴唇问,一边假装专注地望着果酱盒。“以后怎么样呢?”萨宁反问,打了个喷嚏。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觉得他故意打喷嚏来欺负她,虽说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她却见怪了,生气了。“你们这里真好!”萨宁富于幻想地说。“还不坏……”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气还没消,便矜持地回答。可是对于儿子赞美住宅与花园,她却很高兴,因为像对可爱的亲人一样,她和这些东西都处惯了。萨宁看了看她,便思虑着说:“如果您不拿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打搅我的话,那就更好了。”讲这话所用的温和声调与这句得罪人的话相互矛盾,弄得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知道她是该生气,还是该笑。“我该怎么看待你呢,”她惋惜地说,“你在小时候就那么不正常,可是现在……”“可是现在怎样?”萨宁高兴地问,仿佛指望听到什么非常愉快、非常有趣的话似的。“可是现在完全好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尖刻地回答,又挥了挥勺子。“哎,那就更好啦广萨宁冷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瞧,诺维科夫来啦。”“人是可厌的东西!”他并非想到,而是感觉到了,因此他想立刻离开所有这些人,离开这列火车,离开浑浊的空气,离开烟气与轰隆声,哪怕暂时离开也好。朝霞已经明显地出现在地平线上。黑夜灰暗的病态的最后阴影,不留痕迹地逃回在原野上逐渐消逝的浓暗中去了。萨宁没有久想,走到车厢台,皮箱也不要了,就纵身跳下车去。列车轰隆响着,呼啸着在身边飞驰而去,大地从脚下离去,于是萨宁落到了路基潮湿的沙地上。等萨宁站起身来,自己笑自己时,列车车尾那盏红色的信号灯已经离得很远了。“这真好啊!”他大声说,满怀喜悦地发出了自由而响亮的喊叫。四周是多么宽广辽阔啊。依然发绿的草地向四面八方延伸成无边无际的平坦的田野,最后消失在远方的晨雾中。萨宁轻松地呼吸着,用充满喜悦的眼睛望着大地的无边无际的远方,迈着有力的大步,朝着明亮而愉快的朝霞,越走越远。这时原野醒来,露出绿色和浅蓝色的远方,顶上盖着广袤无垠的苍穹,于是太阳在萨宁对面冉冉升起,熠熠生辉,宛如萨宁迎着朝阳走去。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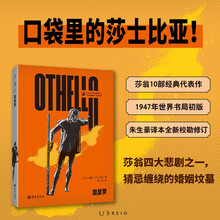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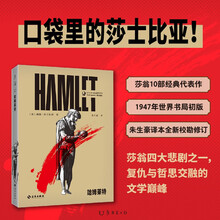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一八七八年出生于小贵族家庭,其父是退役军官。他先在南俄故乡省立中学读书,十六岁时,进入哈尔科夫一所艺术学校。他生活贫穷,不得不给小报画漫画,写短论和滑稽小说。一年后,他便离开学校,前去彼得堡,作了一个地方事务官的书记。一九0一年写了处女作《巴莎·杜麦拿夫》,因其内容暴露学校黑暗而遭禁,后来才收入小说集中。不久,他又写了《暴动》《偷马贼》《笑》等,表达了对沙俄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他初期的创作引起了杂志编辑米罗留勃夫的注意,受聘担任其助手,从此即从事编辑工作。一九0四年至一九0五年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旗手哥洛洛夫》《狂人》《妻》《伊凡·兰德之死》《血痕》《朝影》等。在这些作者自称为“革命故事”的作品中,宣扬强者才有生存权利的思想的《伊凡·兰德之死》,使他出了名;他自己最喜欢的、同样是宣扬无政府个人主义思想的《血痕》和《朝影》,又使他遭到沙皇政府的通缉,险些被处以死刑。一九0七年,阿尔志跋绥夫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萨宁》,在俄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受到尖锐的批判。一九0八年至一九一二年,他又写了小说《几百万》《工人绥惠略夫》《极限》等。他还写过剧本《嫉妒》《战争》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阿尔志跋绥夫仍然坚持无政府主义,对革命抱有敌视态度。他于一九二三年流亡波兰,与人合编反动刊物《争取自由》。一九二七年,在波兰病死。
这位活跃在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文坛上的作家,因一九0七年发表《萨宁》而名噪一时。《萨宁》写成于一九0三年,只因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阻挠才迟发表了五年。这时正值俄国一九0五年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泛滥,颓废文学充斥文坛。而阿尔志跋绥夫的这部长篇小说实为俄国颓废主义文学流派开先河之作,发表后对俄国文坛影响颇大,成为俄国文学史上颓废派文学最著名的代表作。阿尔志跋绥夫在给德国人比拉尔特的信中,表白“《萨宁》是个人主义的辩解”,标榜“小说中的这个英雄是一种典型……但这精神却寄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按照作家自己的解释,作为“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的“这精神”,就是“个人主义”。在他的笔下,萨宁的形象正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
本书的青年主人公萨宁对社会、政治、思想、道德一概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否定一切,否定政治,否定任何社会运动,表现出浓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色彩。他曾“冒险参加了政治斗争,而当这个事业使他厌烦时,他又抛弃了它”。如今他完全否定任何政治活动,对参加社会运动的青年加以嘲笑。他宣称:“世界观不是人生哲理,只是单个人的情绪……明确的世界观不可能存在。”从而否定思想的力量及其作用。他以人的自然本能来否定任何伦理道德,这明显地表现在他处理其妹利达同庸俗军官扎鲁金和进步青年诺维科夫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与冲突的问题上,而他跟妹妹甚至几乎堕落到乱伦的地步。这种虚无主义的世界观表现在萨宁言行的各个方面。他同犹太青年索洛维伊奇克讨论人生哲理问题时,也认为“一切都是空虚的”,“什么也没有”。这露骨地表达了他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和情绪。萨宁对社会的看法也是悲观主义的,随时都流露出一种厌世的思想情绪。他对妹妹说:“人的本性就是可恶的。不要期待人做好事……”而且表示自己“不期望什么”。直到全书结尾,他离开故乡和熟人,还跟送行的朋友伊万诺夫说:“一切都使人厌烦。”“我对生活既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期待。”甚至他乘上火车,仍然厌恶周围的人群,总是觉得“人是可厌的东西!”终于从开动的火车上跳下,落荒而去,以求个人的自由。这个结尾客观上是对萨宁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精神”的一种讽刺。这种悲观厌世的社会观表现在主人公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各个方面,其基础还在于萨宁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