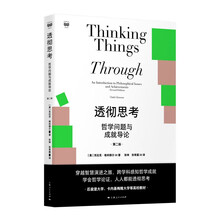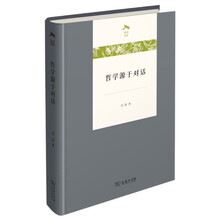在回过来谈谈知性的推理思维时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知性就其本性来说不能把握整个现实,因为它总是从事一种或几种思维操作。它应当分析那种在本性上和内心生活上具有复合联系的东西,提取并考察个别组分。此外,知性受逻辑规律的支配,它按照思维规律来表现思想,以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规则为出发点。但是,正如我们往后将会看到的,心理生活常常是双重意义、多重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心理生活的外在表现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尤其是因为心理事件本身实际上不能同时相互分解。逻辑思维不得不要末推论现实的个别组分(现实不能分解为这些组分),要末片面地对待这个现实,只弄清现实的一个方面。况且,错误的根源还在于只可能去分析这样的现实:它原先存在过,而现在它只是模糊地表明它已被转换过了。这种状况的结果是,知性的辉煌打算,被现实本身化为乌有。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还有一点:灵魂体验,当然还有无意识活动,按其性质来说不是合乎逻辑的。相反,它们往往是悖谬的和非理性的。感觉和无意识的东西中的心理过程决定人们的行为,并通过人们影响历史事件。在这里,心理活动表现出自己的充分的目的性和完全的意义。只不过是心理活动所选择的意义往往与逻辑思维的意义和目的完全不同。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智慧的错误和困惑比心灵的错误消失得快;前者用事件的逻辑可以治好,后者在任何事实面前有时是不可救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看出了知性思维的又一个缺陷:在解决一切问题时缺乏可靠性,却又坚信不疑。知性借助逻辑规则力求理解认识的原理,是为了使它能找到最后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它在作出每一个判断时,总是对自己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在形式上,它在思维的公理规律中寻找可靠性,而在内容上,则在经验中寻找可靠性,同时寻找它的真实原因。“天真的”人、通情达理的活动家把最近的次要的任务当作最终的任务,在其中寻找自己行动和信仰的不可动摇的根据,并且因此而感到满足。敏锐的认识则相反,既不满足于次要的根据,也不满足于所谓的最终的根据。“我当作支撑的初始原因在哪里呢?根据在哪里呢?我从哪里抓住它们呢?我练习思维,因而我的任何一个初始原因就立即引出另一个更初始的原因,如此延续以至无穷。任何意识和思维的本质正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列·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书评中,举了一个意识崩溃的例子。思维规律没有提供关于最终可靠性的知识。这些规律仅仅是思维规律,但是,思维还没有证明:是什么东西在理解现实的规律。精神在思维活动中遇到成为公理基础的规则,而且,如果不破坏自己的思想,精神就不能越过公理。如果真理建立在思维规律的基础上,那它就不会使任何人满意,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规律是否与现实一致。至于谈到借助经验来证明真理,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已部分地谈到过的另一些困难。我们只是在上述限制下才能领会经验,此外,我们还应当有根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发现现实自身方面,经验把我们推进了多远。比如。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常常遭到怀疑。但是,如果满足于思维规律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求助于这些规律而又不能越过它们,那就是荒谬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熟知斯宾塞的理论的,按照这个理论,我们思维的公理只拥有相对真理,因为这些公理产生于在人类历史期间内在未知原因的影响下经常产生着的常见印象。他得出了这个思想,当时他在《地下室手记》)中这样说道:“按照强化意识的正常的和基本的规律,以及按照从这些规律中直接产生的惯性,他得出了关于永恒主题的最令人厌恶的结论:他自己对这些规律的必要性应当负责,而同时又不对它们负责。”尽管有这种必要性,但是精神继续持怀疑态度;可以说,人在他的尘世存在中,天生就具有怀疑感和回避宁静,因为人的知性不相信自己,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认识的渴望,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仅有知性,人类将永远是怀疑和矛盾的俘虏。
我们已经指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研究行为心理学的时候,曾强调人出于他的愿望力求保护其自由的意向。如果人长期只受规律支配,他们就会有一种惧怕,怕失去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能力,怕由于习惯于合规律地行动而不习惯于与此有别的行为,怕丧失自己的自由,使自己的本性变贫乏。于是,他们犯罪,并因而违犯规律,都只是为了确立自由和自行其事的能力。这时,只有看道德立法的内容和服从这种立法带来的结果如何,才能解答合规律的行为是否真的使人的本性贫乏和真的导致不自由。这对于前一个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功利主义,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它事实上能否使人变得更好,它是否有限制人的本性的危险。事实上有谁能说“理性”规定的善对人来说是真正的善,“是对全人类都适用的规律”。要知道,进行逻辑推论的知性只包罗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只知道一部分人的心灵。因此假如规律是进行逻辑推论和仔细观察的结果,那它大概还是不能在习俗的基础上确定真正的道德规律的,因为知识显得不足。并非理性的任何规律都能成为合人的本性的规律。也许,大部分迄今仍不为理性所知的心灵,需要一种与理性规定的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
这样,对伦理学和道德立法的知性论证仍是一个大问题而不可置信。除此之外,即使有了意志自由——我们已经看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为了生活,必须有这种自由——,也不能说道德有必然性和实际依据。也许,意志一般不需要什么监护,而只需要使它唯独能依据其整个本性的动机来充分自由地作出自己的抉择。但也有可能存在一种根本性的道德,意志必须遵循道德规律,并实践这一规律。当人满足一种可能存在的道德规律的要求时,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就在于作出与道德相关的自由抉择。
在道德领域的意志自由,假定有道德规律及其现实要求存在,而它的这种现实性又为全体人所承认,则要求有道德责任。无偏袒的自由——其内涵、其行为目的和希求发挥的作用大小,人本身都能确定——在区分善与恶、在善或恶的道路上选择什么行动方式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两种抉择都需要冒风险,因为作这些抉择都是不确定的。这种选择所以必须在不确定中进行,如我们在实定的形而上学中将会看到的,是由于上帝对人在确定道德选择中没有发生影响。倘若我们对上帝、不死、天堂和地狱有牢固的知识,任何没有丧失健全理性的人所作的选择就不会不准确。但人自己在其心中可自由地决定他怎样对待善与恶。只有充满预感的知识才能供他选择正确的道路。“一个受模糊冲动支配的好人,定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道德规律向人提出不同的道德源泉——神的启示,良心的呼声,人作出的规定和天然的责任要求。人是否对自己的自由仍负有责任或接受哪项道德义务,这是他的事情,不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项义务或否弃道德规律本身,也是有赖于他的。但他在可能发生的末日审判面前承担的罪责也是由自由造成的。人用于存在的法的问题,由此也可能返回他自身,这情况是否发生,人是否需要被迫究责任,那他是不知道的。如果人相信道德义务存在是合理的,但却不履行它,那么反对这种义务的选择就变成了造孽。
人注定要在每个关键时刻作出许多决断。当然,他不可能去实现所有这些决断。“一切都握在人的手里,唯有因为胆怯他错过了一切……我想知道的是,人们最怕什么?他们最怕迈出新的一步,履行自己新的诺言“。他处于像那位农村小姑娘一样的境地,这位?小姑娘说:“只要我愿意,我就攀登,不愿意连动也不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俄国人尤其具有这种对于决断自由的意识。不过这个民族在胆怯中显露出来的粗暴意志力量是会毫不隐蔽地突然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的。
人在否定上帝之后,往往把自己视为宇宙的最高存在物。更经常发生下述情况: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妄想取代上帝的位置,这种情况比在理论活动中多得多,因为人在这种活动中正在成为哲学的唯一中心。应当承认,个人不仅在上帝、道德规律和大自然面前,而且首先是在其周围环境面前,有更高的尊严。
人的观念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视这种哲学。费尔巴哈证明,只有人才是上帝观念的创造者,这就抬高了人的身价。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他能够思维和和感觉,从而使自身异化,使自己和他种角色(如上帝)结合起来并通过它而使自身客观化。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应当坚信,除了他自己,其他任何生物都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对人来说,上帝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费尔巴哈看来,抛弃上帝并不会招致抛弃道德理想的结果;相反,理想依然存在,不过理想也是人设定的。费尔巴哈认为,人存在于与群体的统一之中。
临近19世纪中叶,这些思想在西欧和俄罗斯的文化人和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人们并没有在这个观念上停步不前;人们开始系统地尝试从另一个方面“解放”人们,鼓励人们接受彻底的个人主义。在关于权力观念的一节里,我们探讨了道德规律是如何被抛弃的,关于这一点,后来尼采操心了十年。在此之前,人扎根于群体之说就已经遭到了怀疑,当时英国的启蒙主义者(霍布斯及其他人)开始说明,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是人的意志的唯一推动因素。到了19世纪,所有这些尝试都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观念中结合起来。在德国,M.施蒂纳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他把人看成是模糊的抽象,他把失去联系的任性的个人置于宇宙的中心。
在《地下室手记》里写到一个个人主义者,此人不仅无逊于施蒂纳笔下的人物,甚而至于超过了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哲学的体现者(地下人),是作为“还活着的一代人”的代表而被描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揭示,为什么这种人应当“在我们中间”出现。
应当指出,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是社会隔绝。个人自身被禁锢,完全断绝与他人往来。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这种超乎民众之上的优越感首先与憎恶情绪有关,即憎恶人们轻浮,冷漠,不干正事以及人们的奴性;这是因为他们个性软弱,丑陋,无人过问,等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