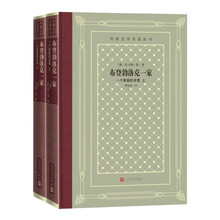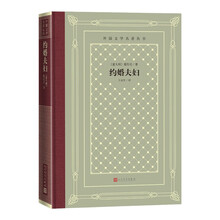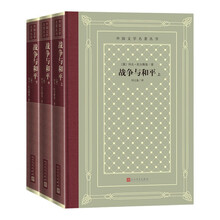悼子冈
我认识彭子冈很早,但她认识我很晚。
子冈的成名是作为女记者,但她的出色在于她有一支文笔。至于她的更出色处则是她的为人。不过,若就她对现代中国的贡献而言,还应当说她是第一批中的,甚至是第一个,当成了新闻记者而且一直当到底的女孩子,一个从向往革命到投身革命而对革命却充满热情而理解不足的天真的女性。
30年代初期,我在申报《自由谈》看到署名子冈的一篇小文,文中提到她住在北平西城一家女子宿舍,捎带了一笔那个宿舍的房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学生》杂志征文中第一名的那个子冈,而这宿舍无疑是我的朋友曹未风新开的秋城女子寄宿舍。于是我去看这位决心花20年时间译莎士比亚的朋友曹未风。他告诉我,子冈本名彭雪珍,是中国大学英文系的一年级学生。我立刻想到那是《中学生》上发表作文的苏州振华女中的学生,大概是叶圣陶先生的弟子。恰在我们谈话时,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女孩子陪着另一位进了院子。同子冈在那篇文中说的一样,她把自行车向墙上一靠,便和她的朋友站在对面廊下谈起话来。曹未风说这就是子冈。隔着窗帘我认识了她。随后我知道她进大公报当了记者。当时有女作家、女编辑,还没有女记者,至少没有能长期正式当大报记者的女孩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想象得出50年前当记者多么不容易,女性对这种职业更是多么难于适应。有勇气的未必有能力,有文笔的又不见得能过忙忙碌碌在各种各样场合会见各种各样人物的记者生涯,受不了几乎天天会碰上的,从报馆内到报馆外,从政治界到文化界,种种方面射过来的责难和闲气。无本领的人,老板不愿用;有本领的人,老板不敢用。可是子冈居然闯开了这一关口,她仗的本身的条件还不是那支笔。会写文章的女孩子有的是。她所仗的是她的天真。我至今也难明白,她怎么能那么相信人,她仿佛想不到世界上居然会有坏人。她不会伤害人,受到伤害时也只是迷惑不解。好人相信她,坏人不防备她,也伤害不了她,因为她不懂人为什么要伤害。她受了气也不会去恼恨别人。她的文并不能完全表现她的人。当然左翼新闻界是另一种情形。抗战初年我在长沙和桂林认识了年纪很轻的高灏和高汾姊妹。她们进了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当记者。那时范长江办的国际新闻社和陈农菲主持的青年记者协会都在桂林。高灏很快成为真正的女记者。可是皖南事变发生,救亡日报关门,她又当不成记者了。终于英年早逝,深可惋惜。女记者的人才到处有,可是能用又敢用而不会被封闭的报馆难找啊。高汾后来到重庆,也成为大公报的女记者。这时子冈已经闯开门路,女记者不稀罕了,但也还不是愉快的职业。太平洋战争时,我在印度认识了在赴美途中的杨刚。我知道她曾用杨缤的名字翻译《傲慢与偏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是作为大公报驻美记者出国的,我在大公报驻印记者郭史翼的办事处见到她。那真是一见如故。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看得起我。我后来才觉得真有点对不起她的好意,我对她说:“你改名为刚,可并不是真刚强。你的傲慢与偏见太多了。你真能忘记自己是女性吗?还是不要那么刚强吧。”坦率的谈话,从世界大势到生活小事。真不知两人怎么会谈得来的。后来我和子冈见面后,立刻发现她和杨刚大不相同。她天真得不知有险,所以能“履险如夷”;而杨刚不行,过不去悬崖峭壁。在郑振铎先生追悼会上我见到杨刚,她说是遇了车祸,神态黯然。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我隐隐感到,像郑先生那样正直豪爽的人会在空中遇难,杨刚这样的强者也在平地上撞车,恐怕她会去追随郑先生。果然不久她便向世界告别了。子冈却像是个大孩子,一直到去世前几年还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她的天真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呢?
直到1948年,我在北平先认识了徐盈,那是由于我的老朋友郑伯彬,也就是杨刚的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丈夫的弟弟。我们在一起谈的是战时和战后的华北经济。我还没有去见和徐在一起的子冈。我随即结婚,才被带到大公报办事处去拜望我的伴侣的振华老同学子冈。大家谈起《中学生》、《自由谈》、大公报,我才发现文实不如其人。子冈和杨刚不同。杨是文学家、诗人,同时是政治人物;而子冈虽是革命者,却不是政治人物。她和我认识或见过的所有女性几乎都不相同。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波涛汹涌的政治和文化界当那么多年记者呢?也许是我错了。唯有她这样的人才能以一叶扁舟踏过风浪而感觉不到什么惊险。
杨刚向我提到过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我在桂林见到她时,她还只能算是个大孩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打毛衣。到昆明见到时,她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上海又见时,她成为一个婴儿的母亲。从此没有再见,但她给我的印象却不可磨灭。她有子冈的天真,又有杨刚的自信。这是难得的“二难并”,可惜并不是好事。她虽过了杨刚过不去的第一关,却过不了更高大的第二关。反而子冈都能过去,可以说是生于天真,没于天真,给她的友人留下一个无法描述也无可描述的印象。这没有她留给国家社会的文字永久,却更深刻也更生动。
对我来说,这世界是有点奇特的。有一些人见面很少,谈话不多;有的人几十年的交情不过是通信,对面谈话微乎其微;有的人仅仅是一般朋友的见面,甚至还不大见面;可是这些人却都留给我淡化不下去的影像。子冈属于最后这一种。这个名字和这个人,尽管在宇宙中仅仅是一闪而过,然而这道闪光是永存的。
1988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