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站台真是一个容易出戏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首歌就叫《站台》,好像是那个没什么大出息的孙国庆唱的吧?闹哄哄的,没有唱出感觉。听说有那么点小意思的“地下导演”贾樟柯也拍了个名叫《站台》的电影,拍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看到。这些年来,我来自生活的对于站台的记忆竟是因为儿子在某个年龄段的特殊癖好。
在他三到五岁的那两年中我有时要应他的要求到火车站去,目的是看火车。那两年中我的亲戚朋友一定都觉得我忽然变得过于热情了,只要他们有坐火车去外地出差或旅游的机会,我都会在电话中主动而又坚决地提出要到火车站送对方,不论对方如何表示这没有必要,也最终会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看到我带着儿子来送他们了。有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但儿子要看火车的那个瘾强烈发作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以接人的名义买一张站台票,就那么进去了。花一块钱让儿子看一次大火车,看着他面对轰隆隆的进站火车欢呼蹦跳的场景,我就觉得我花点时间这么看似无聊地来一趟是很值的。
细细是个好编辑,这是我最终获得的一个印象。每期杂志她不是发稿最多的,但是非常稳定。她不是对杂志没有想法的,只是不在公开场合说。那时候下班以后我们总是同路回家,她在公共汽车上讲起杂志该如何搞也是一套一套的,让这份杂志发行量上扬知名度暴涨的那个“十差作家评选”的策划就是细细最先提出来的。细细到杂志社来之前我就听说这是一个“才女”,她写那种叫做“青春美文”的东西,发得满天都是,在读者中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而在杂志社内部她却成了一个著名的“怪人”,有一个关于她孤僻的段子不知是怎么传开的:说她住在父母家,有天晚上洗澡,在浴室里一呆就是两个钟头,急得父母和她两个妹妹不断去敲门,敲得多了,她还很不高兴。她二十大几的人了,没有男朋友不和男人约会也是被议论较多的,说她接听男士的电话,有两句著名的台词:“不吃!”“不喝!”——有人推想电话中的对方一定在说:“请你吃饭好吗?”“那我请你喝茶吧?”我听到一种说法是:她如此对待男人的盛情是因为初恋遇挫,挺好的一个男孩,仅仅因为出生于农村而被自己的父母活活拆散了!
在这个封建家长式的杂志社里,由一些“灵魂的妓女”构成了一种叫人恶心的气氛,就是我即使和老板没什么事儿,也要暗示别人我曾给老板洗过内裤。人们也传诵着细细的“另类壮举”,有一次老板请几个人吃饭,其中也有她,到饭桌上大家惊异地发现她根本没有来,有狗腿子偷偷跑出去打电话叫她,她的回答很简单:“不吃,吃饭无聊。”——可爱的女孩,在她眼里老板和那些约她吃饭的男人没有区别。
从她身上我意识到:所谓“怪人”真是人民群众发明出来的一个最阴险的词。她“怪”么?一点也不:无人可爱就不爱,多余负担全省了。我曾想过:我如果先她之前离开了这家不正常的杂志社,我就还算是个正常的男人,好在最终的结果如我所愿。
足球界闹腾“恐韩症”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也尚未终结。谁是这一词的发明者,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我想这近20年来的他一定经常性地处在一种得意洋洋的情绪里,也许当初的命名纯系偶然,但近Z0年来中国国家男足逢韩不胜的历史却将这一词提升到了预言的高度,此人也便成了预言家。若编一本《当代成语小词典》,如果编得还算权威的话,我想“恐韩症”一定会赫然在目。
作为一个写诗的,我深知语言这东西的“魔力”。诗歌界形形色色的扮酷者历来不少,诗里诗外地扮酷,但也不是全无禁忌——比如说“死亡”,现在似乎没人敢在这个词上口无遮拦了。为什么呢?因为数年以前死去的几位诗人都在其诗里留下过“预言”的——海子说:“我是众尸之王”,他便成了近20年来诗人自杀的一个先行者;戈麦说:“我要沉入那最深的海底”,这几乎是对他自杀方式的一种设计——最后他投湖自尽。从此,没人敢在写诗时乱给自己开玩笑了,死亡的玩笑。
我们也用不着谈得很玄,关于语言,关于它的“魔力”——我想那是一种现象经过我们的口变为语言的现实之后对人心理产生的一种反作用力,一种强化性的暗示作用。回到“恐韩症”,是逢韩不胜的事实造就了这个词,到了下一代球员则成了比赛还没打呢就先知道世上有种“恐韩症”,心理上难免就会起微妙的变化,中韩足球对抗中许多未战先输的活例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是“恐韩症”帮韩国队打败了我们,是“恐韩症”这个词让我们患上了“恐韩症”这种病。
后来,听说“韩流”来了,先是一些蹦蹦跳的歌,再是一些黏黏糊糊的剧,然后是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没那么冷啊,也没那么酷,非说得那么危言耸听干吗?20年前一个青年的装扮若是像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华侨就是一种时髦,15年前是港台人,10年前是日本人,如今是韩国人,这些课好像非得一一补上。正如韩国足球的全部力量也抵不上“恐韩症”这个词,所有花在那些歌、剧、衣服上的广告费用也没有“韩流”这个词值钱。“韩流”是中国人为韩国商品发明的—句威力无比的总广告语,与此同时,韩国人在干吗?国民在抵制日产汽车,一百名电影导演剃了光头在汉城的广场上集会,号召国民不要走入影院去看美国大片……
从“恐韩症”到“韩流”,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文化心态中一些浮躁的东西,浮躁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但其中暗藏的浅薄与自轻自贱却还是让人大吃一惊!过去时代蒙昧的中国人是把自己编成神话来吓自己玩,开放时代开化的中国人是把世界编成神话来吓自己玩,都21世纪了,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种无休无止的自我恐吓呢?
十年前她往巴塞罗那的跳板上一站,一块水淋淋的金牌就跳到她脖子上了,记得是那时还在世的母亲很喜欢这个女孩,而我对她的小男孩模样则毫无感觉。
六年前出现在亚特兰大的她却让我有着无比的惊讶!是女大十八变啊!那时的她已经出落为我记忆中惟一一位能让我感受到性感的干体育的女同胞。
两年前悉尼奥运会上的她已经是在创造奇迹了,我曾经以为”、“高敏神话”是牢不可破的,到了她这儿就跟玩似的!双眼放电的我心怀的一片肃然。
我以为伏明霞是有观音相的。有观音相的女人我在生活中见识过两个,命都好得不得了。一个是我之初恋,一个是我在杂志社兼职时的一位同事,如今满街都是想嫁大款的女孩,更有甚者整夜都在酒吧里候着,可终是不得。这两位我可从测听人家嚷嚷过,还死活要嫁给我等穷人,还在我等这里不受待见,一抹泪,一跺脚,走出门,年轻英俊的正宗大款已在门外恭候多时了!现在两位都已为人妇,为人母,一个远在异国他乡,一个近在本城富人区,过着恬淡悠闲的日子,偶尔想起我等穷哥们,就如同想起她们年轻时路过的贫民窟公厕。
由此我认定同样具有观音相的阿霞妹妹今生的命也将好得不得了,就她而言,单纯的大款是用不着嫁的,如能最终嫁与香港财政司的梁哥那也真是造化!至少是离农村大集一般的三里屯酒吧远了,离无聊北京的“名人俱乐部”远了,离时髦的摇头丸远了,离什么也没教会她的清华大学远了,离没文化的中国体育界远了,再蒙头蒙脑地穿上一条写满fuck的裤子时,旁边有人能够指出来——毕竟丫头底子薄啊!底子薄的傻丫头最好不要待在底子薄的地界和人群里。
这真是:足球圈少了一位名家属,好女孩多了一份真幸福!
而咱们一帮老爷们在这儿家长里短地嚼舌头,无非也是出自一种纯朴善良美好的心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天下好女孩找到好主!
我在外地的朋友以北京为最多,每次在北京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似乎总能成为他们的同情对象,这份同情也总会体现在相似的一句话上:你怎么还在西安呆着呐?——或者直接就是一句:干脆到北京来吧!
这个建议到目前为止在我这里尚未奏效,事实是我对此项建议从未动心。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我居住的城市缺少了我生活必需的内容,就跟人人倾羡的北京相比,它也不缺少什么。柴米油盐,声色犬马,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朋友诗人李亚伟对我说:北京缺乏市民生活的传统——他可说得太对了!这个传统是被另一种叫做“文化”的东西遮蔽并取代了的。没有市民生活,只有文人时尚——这便是我眼中“文化中心”的生活格局。华灯初上的时候,满北京都是所谓“文化人” 的饭局,我曾跟随两个朋友在一个晚上赶过四个饭点——那真是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累啊!从第四个饭点出来打车回住地的路上我曾对这两个朋友抱怨说: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如果单单是累,那只有傻子才会去赶这些饭局,用我的话说:饭局不过是北京文化人相互之间送温暖活动的举办地。早两年我在这种场合初感温暖时我也是颇为喜欢,发现自己可以呀,被如此之多的人敬着。后来我是渐渐发现在那个场合,其实人人都是爷,因为那种互送温暖的气氛让每个人都有腾云驾雾之感,这种方式的生活也便成了我眼中不折不扣的“伪生活”。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夜晚,也有类似文人的饭局,有所不同的是:我是本城带有强烈农民气息的文人眼中的非文人,人家一般不带咱玩。另一方面,文人的稀有决定了此类文人饭局无法构成一种时尚(早被非文人光着膀子热气腾腾直奔吃喝的场面淹死了),所以与大多数的文化人也没有关系。我曾问过自己:这样的文人饭局我需要吗?我出于本性的回答是:不需要。诗人于坚曾在一篇文章中发问:李白和杜甫、庞德和艾略特有没有一起参加过在某风景名胜之地举行的笔会——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当一位深爱着三里屯的北京文人告诉我说他之所以要常去那里是不想和生活脱离,目的还是为了写作——我真以为他讲的是外星人的逻辑和道理。
从去年到今年有如下消息相继从北京方向传来:某某到外地租房写作了,某某某搬到农村去住了。在某个诗歌网站上还看到一些“70后”的诗人为“上山下乡”的这位小爷所写下的一组送行诗,那种煽情的气氛真是把人大牙都要酸掉!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首有着这样的标题《送某壮士赴某县》,读罢我忍不住在底下留言说:应该是送某懦夫到某县吧——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这位小爷完全是因为受不了在北京巨大的生存压力才做此选择的,既非得道而为的壮士
又非随心而动的隐者,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生活失败者。文学、写作被当成最后的遮羞布。 唉!对我对你,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是在别处的,别处的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累!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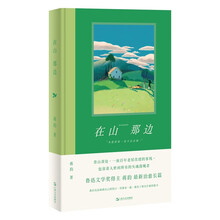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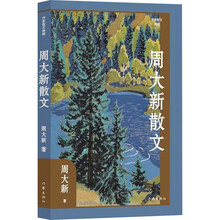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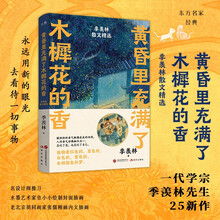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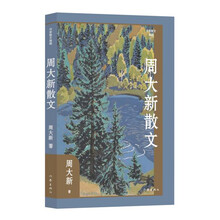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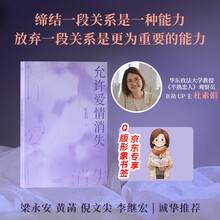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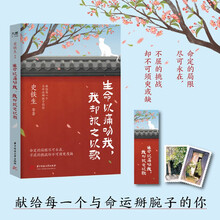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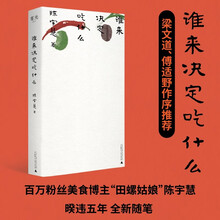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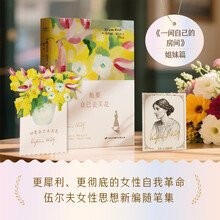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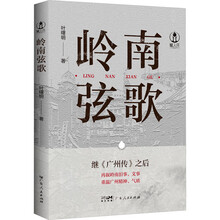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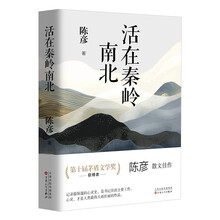
一位作者为其新书撰写“自序”的时刻,也就是这家伙最容易上赶着装孙子犯虚伪之时——对此,我早有警惕。好在原本就不是写本小书就以为发现了地球上一半“真理”的那路货色。
本书是我的第二本随笔集,选收了本人在1999—2003五年间散发于各地报刊的数十篇闲杂文字:有生活小品、文娱酷评;俗至足球,雅及诗歌;杂七杂八,不一而足……现在集中成册,得以堂皇出版,似乎也找不出太大的理由。
网上常遇老读者,还在念及我出版于六年前的那本《一个都不放过》——其中涉及的话题恐怕早已作古,文字造成的快感却难以释怀……要写就写叫人记住的书原本就是我的自律,每每感念于此,我知道惟有新著可以图报。
六年前,我劝自个儿闲文少做,但六年下来却又做出了一堆,如果出书,也将不止于一本。未料却遇诸多不顺,要命的阻力总是从斜刺里杀出,连个“自序”也写过好几个没用的。现在终遇良机,也是本书命中注定的缘分使然。谢天!谢地!我还当在书外谢人!
等急了吧?我的读者——鲁迅称得更精彩也更准确——我的“主顾”!
“主顾”们知道:我是主动做诗,被动为文——闲文或曰“随笔”都是信我爱我的报刊编辑们长年不断“催命”的结果,尽管我比六年以前更为重视和爱惜自己的闲散文字(是否老了的缘故?),但也将继续沿袭此种被动,现如今主动出击的一方面又添加了熬人费时的长篇小说进去,所谓“随笔”就将少下去了吧?我不知道,只想在此谢谢我的编辑们!并不完全拒绝你们日后的“催命”。
已经说多了,好在无“大话”。
打住,并请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