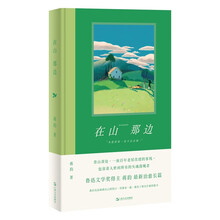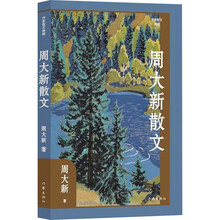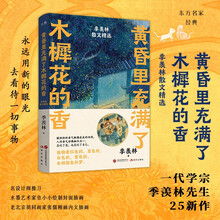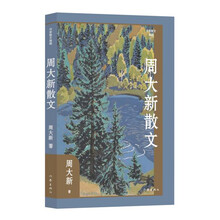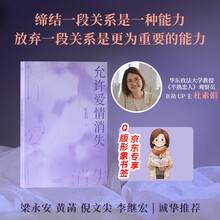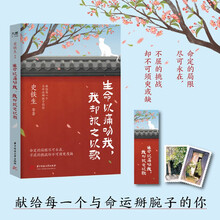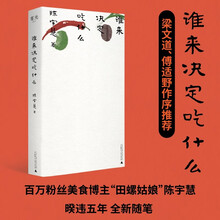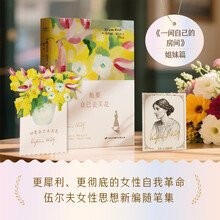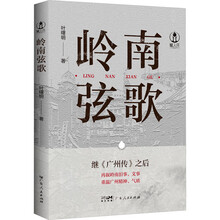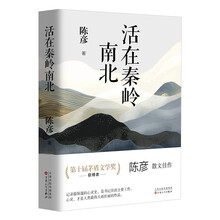侨居东京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去过上野的,特别在赏樱时节;去过上野,一般就见过“恩赐公园”里竖立的那尊铜像,虽然可能只随口问一声那是谁,还牵着条狗?铜像看上去脑袋异常大,顶上常落着一两只鸽子或乌鸦,挂了些它们的发白的屎迹。那就是西乡隆盛。
1877年,大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日本上陆,正赶上东京大学建校,又赶上西乡隆盛造反。他在《使东述略》中记述: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租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这位西乡是风云人物,文图并茂的历史书上必有他的照片,头大眼也大。兵败,在城山自杀。百姓对专制不满,世间便盛传天上出现“西乡星”,其实是时隔一百五十年火星又接近地球。西乡反政府不反天皇,大概从来没想过鸟皇帝人人做得。死后三年,明治天皇追谥他正三位。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记起几年前陈平原在《阅读日本》的随笔里写过“西乡铜像”,是因为读井泽元彦的著书《逆说日本史》,他的“怨灵”之说或可解释这种“豁达”现象。
井泽说:推动日本历史的是怨灵。所谓怨灵,就是在政争中失败而死的幽灵,当然含冤衔恨。最典型的冤魂是菅原道真(845—903)。时当平安初期,道真官居右大臣,遭左大臣藤原时平谗陷,被醍醐天皇贬黜到远离京都的太宰府,贫病交加,死在了那里。他死后,“怨灵”作祟,雷击宫殿,藤原清贯等大臣当场毙命,吓得醍醐天皇退位。天灾频仍,“举世云,营师灵魂宿忿所为也” (汉文编年体史书《日本纪略》)。当时民间盛行“御灵会”,为“怨灵”安魂。京都有北野,一夜之间长出松树数千株,于是人们在那里建天满宫祭祀,奉道真为天神。“天满”,是“嗔恚之滔满天”的意思。道真死后二十年,皇太子猝死,朝廷赶紧给他平反,追谥正二位。一谥再谥,道真的冤魂当上正一位,位极人臣。为失败者安魂,让他高高兴兴在另一个世界里做鬼,别跑到人世间为害,这种“怨灵信仰”,井泽说“才是使日本文化发达的动力”。
史学界并不否认平安时代冤魂怨灵对历史的影响,而井泽元彦认为始自神话时代,历史的车轮一直由厉鬼们推动着。他用“怨灵信仰”解说一切,虽然更像是推理小说家的操作,却也蛮有趣。他说:《源氏物语》是人类第一部长篇小说,近乎奇迹,为什么偏偏产生在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呢?原来它也是“怨灵信仰”的产物。《源氏物语》问世于平安时代中期,描写平安初期和中期的宫廷及社会。主人公光源氏,据说实有所指,即企图把女婿立为皇太子以夺取藤原氏权威的源氏。那时代重臣都是把女儿或妹子奉献给天皇,当皇帝国戚,操纵国柄。作者紫式部是藤原氏女儿身边的女官,好像和藤原氏还有点男女关系,却居然把政敌源氏写得极尽荣华,甚至当上准太上皇,岂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更可怪的是藤原氏不但不恼火,反而还提供贵重的纸墨砚台,予以支持。这就是因为他排斥了源氏,大权独揽,朝廷的政争从此往后都是他藤原氏族内的事了。获胜之后,用虚构故事来满足失败者,既是“慰灵(镇魂)”,又是慰藉胜利给自身带来的不安和内疚。日本接人待物彬彬有礼,爱说些个恭维话,莫非也出于“怨灵信仰”的心理?
其实,井泽元彦的“逆说”并不是新说。陈平原在《西乡铜像》一文的附记中就提及:“据柳田国男称,在日本,作为个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还必须是悲剧性死亡。而新政权为与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抚失败者的亡灵。”但他没有特别从这一角度阅读西乡铜像,可能因其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对于敌人,中国人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
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白花花的银子,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赔给了日本,据说等于它四年的财政收入。土狭民寡的“蕞尔小国”一下子富了起来,于是往欧洲增派留学生。其中有一位,时年三十三,个子矮矮的,被文部省派赴英国“调研英语教学法”。他就是日后成为文豪的夏目漱石。
漱石走在伦敦街头,迎面过来一个奇怪的家伙,却原来是他本人映在橱窗玻璃上的身影。周围净是身材高大的美男子,教他自惭形秽,满怀自卑感。漱石是1900年乘船到英国的,吞吐了两年一个月大都会烟雾。对于漱石文学来说,这两年至为重要,但英国给他的印象坏极了,深恶痛绝。要是按他自己的意志,一辈子也不会踏上英国一步。自卑感不仅来自身体的差异,更来自经济的困苦——他给夫人写信说:日本的五十钱在当地几乎只等于十钱、二十钱,十日元花两三次,一眨眼就化为烟。他在伦敦一连换了五处住所,不得安生,全然没有周作人对日本“兔子窝”的怡然自适。两年中一年有半住在大停车场附近的民家,除了逛逛旧书店,几乎杜门不出,耽读书籍,准备回国后打算到大学任教的讲义。漱石本来喜好汉学,讨厌英语,但在“文明开化的世间”当不了汉学家,只好把汉籍统统卖掉,转向英文学,“要用英文写大文学”。不过,那时并没有英语热,东京帝国大学办英文科已历四年,只有两年各有一人报考,漱石成为第二个毕业生。没有同学,这种孤独使他研究英文学伊始就心存不安。目睹英国的商业主义和拜金风气,他更感到幻灭,神经衰弱也益加严重,以致周围的人怀疑发了疯,但他却从此恢复自我,不再过高评价英国人,进而以自己为本位批评英国文学。1907年印行的《文学论》被视为“漱石对于外国文化的独立战争宣言”,他在序言中回忆:“住在伦敦的二年尤为不愉快的二年。余在英国绅士之间,如同一条与狼群为伍的卷毛狮子狗,日子过得甚凄惨。”直到晚年,他还在讲演中“说真的,我不喜欢英吉利”。
只要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人多少都会有自卑感,也许这正是自知之明的表现,只不过表现得较为消沉。在日本作家的身世和性格中常见这种自卑感,例如太宰治。他从不遮掩自己的自卑,反而展现乃至夸大,以赢得同情。三岛由纪夫叱责:“太宰所具有的性格缺陷,至少有一半是可以用冷水磨擦、器械体操或者有规律的生活来纠正的,应该靠生活解决的事就不要麻烦艺术。略玩一下反说,不想治愈的病人不配当真正的病人。每当接触太宰文学,每当接触那种残疾人似的孱弱文体,我感到的是这个人对强大的世俗道德立马现出受难表情的狡猾。”其
实,三岛也怀有强烈的自卑感,只是和太宰正相反,他一生都大加掩饰,当然也连累了艺术。三岛矮小,找对象的条件之一是女方穿高跟鞋也不可以高过他。他“用冷水磨擦、器械体操或者有规律的生活”改造肌体,但运动神经不发达,剑术到底不高明。从文体的华丽到肉体的健美,三岛一生执著于虚构,最终演一出武士剖腹,了却了自卑情结。读井上靖的小说《翌桧的故事》,知道有一种常绿乔木叫“翌桧”,这名字的意思是明天变成桧树,但永远变不成桧树,可悲的宿命就不免令人自卑。小说用翌桧作象征,描写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有不少自传成分。井上在《我的自我形成史》中说过:“由于成长在这样的伊豆山村,我从小对城市、对住在那里的男女少年抱有城市孩子们无法想象的自卑感。而且,这种自卑感变换种种形式支配我这个人,直到很久以后。”
以夏目漱石为例,似乎我们更多些理由厌恶日本,当然也可能出于自卑感。说不定因此能确保不当周作人,只是别忘记,对英国的反感使夏目漱石成其为夏目漱石。
缩小的对立面是扩大,扩大得玄之又玄,就变成夸张。在文学艺术里,夸张是表现手法之一。中国文学史上把这种手法发挥得神乎其神的,是诗仙李白。让他愁起来,头发能愁长“三千丈”。三千丈,这一头白发从富士山巅垂挂下来,可以打三折。“白发三干丈”,千百年前的诗句迄今在人们的口头上活蹦乱跳,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语言文学所独有的奇迹。
诗人作诗,往长里说可以夸张,往短里说也可以夸张,如“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或许真是受中国影响,日本人作汉诗的时候也会大气起来,如“千年积雪拥蓬莱” (室鸠巢,1658—1734),“芙蓉峰上一轮高” (荻生徂徕,1667—1728),“谁将东海水,濯出玉芙蓉;蟠地三州尽,插天八叶重” (柴野栗山,1736—1807),虽然多是从中国诗词套来的。从现实生活来看,日本人确实喜爱小东西,称之“小”日本一点都不错。中国地大物博,人心就开阔,大大咧咧。即便缩而小之,也不是日本人那种精细小巧的感觉,读来也别有气魄,如毛泽东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富士,以前也写作不二、富慈等,一说来自阿伊努语,是“火”的意思。富士山是一座圆锥形的孤峰,坐落在山梨和静冈两县的地界。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乃日本最高峰,自古被当做日本的象征。有一幅照片,富士山下奔驰着新干线列车,似乎是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海报。东京都内叫富士见的地方不少,就是能望见富士山的意思,但现在大都被高楼遮挡了。此山巅峰陡峭,上有直径约八百米、深约二百米的喷火口,那就是栖老神龙的洞中渊。山麓平缓,乘车可直达“五合目”(从山脚往上爬,山路分为十段,“五合目”即第五段)。山上遍地是火山喷发的灰渣滓,登临不如远眺。富士山之于日本人,是一个夸张。
日本人常说,中国人爱夸张,“白发三千丈”。被人家拿李白的诗句评头品足,很觉着舒心,虽然到了末流,也生出许多的阿Q。国人说话确实好夸大其辞,莫非李姓第一多,大家都带了些太白遗风?这种根性在大跃进年代发挥到极致,什么超英赶美,现今想来还不免教人脸红。然而,某些日本人接着说,南京大屠杀是“白发三千丈”,可就是别有用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