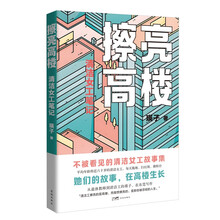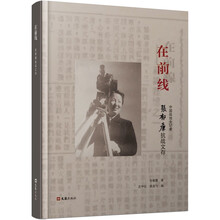每次遇到填什么表格,我总要对着“籍贯”一栏发呆。奶奶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宁波人,因为,爷爷的爸爸是“老宁波”。可是,就连爸爸都忘了宁波老家是什么样子了,我更只是在地图上看见过它。而留在记忆中最亲切最美好的地方却是那:撒满碎银般的盐滩上,静静地睡着一条清凌凌的大河:大理石般的夜空悬挂着一眉勾起簇簇芦苇梢的镰月;从绿荫荫的蒲儿草丛中不时地惊起一群群野雁……<br> 奶奶警告我:“表格上不准填你是苏北滨海县人,谁不嫌弃苏北人?在上海,苏北姑娘对象都难找。”这倒是真话,表哥谈恋爱,和一个“她”好了两年,就因为她说话带苏北腔,姑妈不同意,吹了,表哥至今还郁郁不欢。姑妈鄙弃地说:“你不知道,苏北人最穷了,又粗陋又低贱……”哦——我听了就像自己的亲娘挨骂一般地羞耻和委屈,倘若苇叔和苇姨还在,一定会骂我是不肖子孙的…… 睡在盐滩上的大河是射阳河,苇叔趁着暮色,把临产的妈妈送上躺在河湾里的小船时曾说过:“嫂子,这河是后羿射九日的一支神箭划出来的,生在河中的娃娃一定有智有勇……”可我怎么连承认自己是苏北人的勇气都没有呢?<br> 苇姨的腰身又柔又细,一扭一扭地像扭秧歌,她手中的两把桨轻轻地剪开绿绸般的水面,小船儿像一阵掠过水面的清风跑得飞快,把沉闷的炮声甩得远远的,空气中漫起了甜蜜的花香,蚕豆开花像婴儿待哺般地张着嘴,月亮从芦苇丛中升起,弯弯的,很像苇姨的眉毛,一颗汗珠就挂在眉梢上。苇姨松了一口气,把小船驶进蒲儿草丛中,扑棱棱惊飞一群栖息的野雁,于是,我就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苇姨的脸,眼晴里嵌着两颗星星,晶晶亮。<br> 我不知道刚落地的娃娃会不会有记忆,小时候的事妈妈常常说起,说得多了,就像是自己的记忆一般……几天后的半夜,爸爸骑马赶了百儿八十里地找到我们的小船,部队要转移,他来接妈妈。苇姨抱起我,喜滋滋地招呼爸爸:“快看看吧,你的小雁儿!”可爸爸不看我,也不看妈妈,却死死地盯着苇姨,瞅得苇姨脸都红了。妈妈很生气,正要张口责问,猛然间看见爸爸两只攥紧的拳头在发抖,心中忽地明白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苇姨的脸渐渐地由红转白,声音像风中的芦叶在飘:“……是老苇他……没了……?”<br> 泪水中的苇姨,就像一株浸在河水中的蒲儿草,苍白、柔弱,摇晃着……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