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就是不偏食
以教育的观点看,“通识”就是要防止学生“偏食”。如果学生求知欲
强,兴趣范围广,应付功课之余,有把闲情寄托于课外书的习惯,那不需老
师指点,已得通识教育的要义了。
我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念大学时,外文系的学生除大一国文外,还要必
修中国文学史。因是文科生,你要毕业,非选修本科目以外的一些科目不可
,如社会、经济、心理、历史、哲学或政治。用意就是防止“偏食”。四年
下来,本科生对本门的知识,所知也仅限于皮毛。跨系跨科去选修一两门课
,能获益多少,更不能存奢望了。不过我相信,既要在“地球村”的现代社
会生存,对世事一知半解总比不知不觉好。
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是一种专门学问,是学者专家才能深入讨论的
题目。不过我们门外汉,只消略识皮毛,也受益不尽。颜纯钩在《柯灵先生
的两封信》中透露,柯灵晚年要写的《上海沧桑》,一直搁着没有动笔,原
因是老先生不断为讨他序文以高身价的“朋友”所苦,几十万字的稿件一本
接一本地送上门来要他过目。柯灵如奉行机会成本守则,《上海沧桑》说不
定早已面世了。
《信报》近有王兼扬一文,说到香港商科毕业生求职面试时,对本科知
识的掌握都很有把握,但当谈到其他科目或常识问题时,应变和自信都明显
比外地毕业生逊色,他认为“缺乏通识和常识是其中主因”。
作为认识大干世界的门径来说,通识教育不能取代日常读报的习惯。跨
国大公司在香港招聘,如果老板是美国人,“考官”说不定会问,历来对Bi
g Business较“友善”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通识、常识关乎我们的百年
大计。大学三改四,多了选修科的空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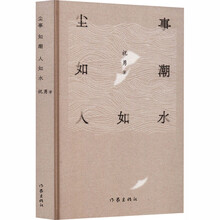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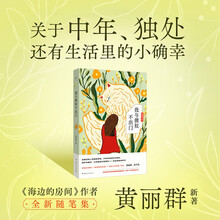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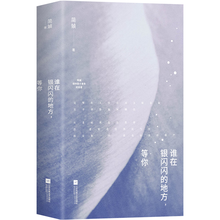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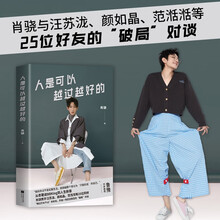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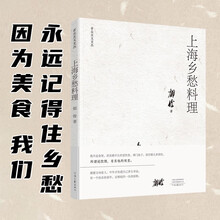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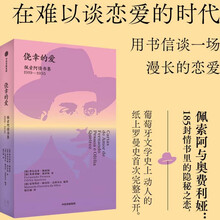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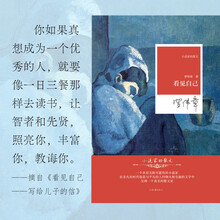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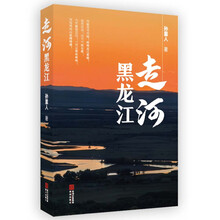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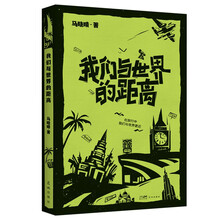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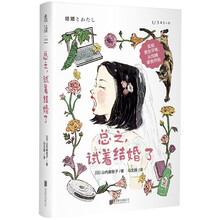
一呷,造就了学术和艺术的一场厮磨;敷着薄霜的玻璃杯浮起柠檬黄的满月
,荡漾的是英格兰树林的冷香和他笔下索非亚·罗兰故乡的橄榄梦。那是刘
教授吃过马铃薯的日子之后燃点一炉烟火的境界,跟他的文字一样动人,跟
他的学问一样清幽。
——董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