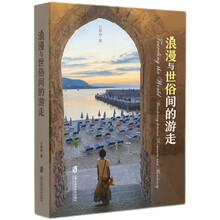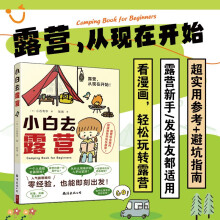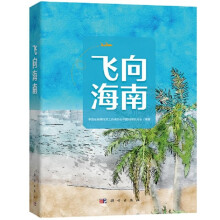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到牛棚找安静和许晓。<br> 爬上斜斜的木梯,上到二楼,这是我第一次上到牛棚的二楼,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苍老破败,漆黑阴森,而校毓和安静,还有已经离开了的老Peter,以及正在值班的许晓,都曾住在或正住在里面。楼上和楼下一样大,绝大部分空间都荒芜着,在眼下寒冷的冬天,只剩两个小女子栖息着,想想都毛骨悚然。<br> 许晓住在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里,是Peter先前住过的。她弄了一些粉红色的无纺布,掩住了旧木墙中间的一条,旧的单人床呆呆地停在墙边,床头上夹着一支20世纪60年代的台灯,军绿色的,床上铺了电热毯,还有许晓从广州空运来的杜邦棉被和枕头,许晓说只有睡这个她才能睡得着。我立刻就想到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棉被边缘闪烁着一双呼啦啦的眼睛……对面墙边的地上放着一张单人床板,上面零乱地丢着睡袋、面膜、书籍、袜子等一干杂物,都是许晓的。<br> 安静住隔壁大的那间,大得离谱,可能是因为东西太少的缘故,望进去黑洞洞的,不知道那黑暗的尽头还摆着什么,床近窗摆着,枕头边有一张小安楠的照片,这是唯一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温度的东西。<br> “这房子太老了,阴气太重,要时常找男人回来住!”我随口荡着,安静和许晓一脸的坏笑。<br> “想什么呢!赶紧去招募几个瞧着顺眼的老实人回来住住,哪怕做免费的客栈,也凑个人气,暖和暖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说。<br> “那从明天起我就去找,满世界地找,嘿嘿…许晓。<br> 次日,来了一个江南人,做广告的,眼下正琢磨着要改行,也想在个什么地方经营个客栈什么的,一身短打扮,二郎腿翘得老高,长得整整齐齐,有板有眼,怎么看怎么不像做广告的,怎么看怎么就像个开店的,那种大通铺的简易旅店,连吆喝带打理,绝对一全能选手。那人很健谈,说了什么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他一直在说,说个不停,起身站着说,绕过炉子停在炉子边上说,往门口走,边走边说,站在门口还在说,已经出了门,又把脑袋丢回来说,坐在不同位置的人,都不得不跟着他的脚步拧着脖子追着听,后来终于“嗖”的不见了,如果不是给尿憋的,我保证,他还得说个不停。看他阳气十足的样子,就问,“你有地方住吗?如果没住处,就住这儿吧,楼上有房间若干,都空着,你可以在里面支帐篷,开头灯,睡睡袋,说梦话,总之呢只要每天打水扫地,给她俩烧烧饭就成,不收你钱。”<br> 那人爽快,一口答应明天就搬过来,临走的时候还特意邀请我,“你明天也一道搬过来住好了啦!”我没好意思笑出声。<br> 第二天傍晚,我正忙着,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嗯--你那里能烧饭不啦?”<br> “啊?”我一头雾水。<br> “啊--我就是昨天我们一起聊天的那个,在牛棚,你想起来了哇?”<br> 他。<br> “哦!”我。<br> “你那里能不能烧饭!?”他。<br> “烧饭?烧饭!烧饭我这里不行,我住宾馆,没火,不能烧。”天!那小伙子当真了!<br> 是许晓把皮球踢过来的,我脑子一时迟钝没想到更好的法儿,就一口把人家回了,撂下电话才觉得干巴巴的,但正忙着也就没多理会。<br> 我是没在场,据说那天这哥哥是大袋小袋鱼肉、蔬菜、豆腐、水果,没少拎,一脸喜气洋洋,像来过日子一样,也不知道许晓和安静后来咋把人家给对付走的,且是一去杳无音讯,现在想想真是十二万分地抱歉,一盆冷水把人家对美好生活的热望给浇了个透心儿凉。人家一定以为咱们香格里拉的草寇没信誉,唉,悔之晚矣。<br> 还有一天晚上,除了我们几个私房朋友,牛棚没什么客人,正觉着太清闲,来了一伙儿男孩子,大都十四五岁,是来给其中的一个小胖子过生日。小朋友们很有礼貌地邀请我们一起吃蛋糕,安静送了他们每人一杯成人饮料。<br> 吹灭了蜡烛,一个个小家伙立马儿原形毕露,他们开始用奶油疯狂地涂抹到别人脸上,一开始还仅限于内部创作,不大会儿功夫,就扩大到了见者有份。我一脸的严肃,侥幸逃脱,许晓没能幸免,被抹成了圣诞老人。还有正在专心打桌球的花哥,也被强行套上了奶油面具。<br> 战事终于平息了,和平的音乐,远远地响着,我坐在吧台里绑着漂亮羽毛的高脚凳上,吧台外围着一圈少年孩子,正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可乐,操着乡音,说着同学故事,都是一副大人样儿。许晓说,在烛光里的我很像个有号召力的老师。<br> 不一会儿,其中唯一的一个混在大孩子里的小朋友,坐过来探着身子,隔着吧台用普通话对我说,“我给你讲一个很好玩儿的事情。”“说。”我。<br> “我们班有个同学,今天他和我说他想要自杀,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那孩子。<br> “为什么?”我。<br> “因为--”他喝了一口可乐,接着说,“因为他的英国女朋友走了,他很难过,就想要自杀,你说好不好笑,太好笑了!呵呵呵…那孩子。<br> “你几年级了?”我好好地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小朋友。<br> “我四年级了!”他镇静地冲我伸出了四个细小而坚定的手指。<br> “噢--”我脑子里空空的,有点儿弱智。<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