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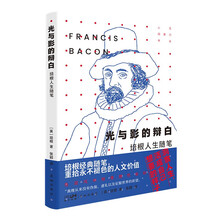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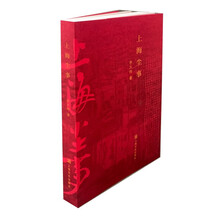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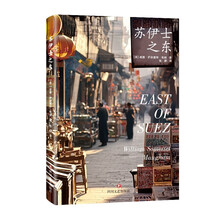
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
林语堂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中山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诌其短见。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猛进》第三期答鲁迅语)。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气洋癖,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觑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乎时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时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先生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岂明先生已经说过(《语丝》第十九期)“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诚然应希望大家注意。
提倡“精神复兴”我觉得是今日言论界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二五,三,二十九
(选自《翦拂集》,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