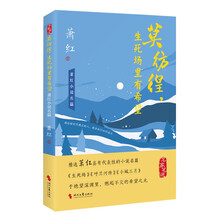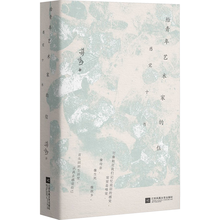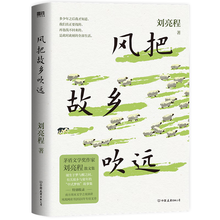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回去吧!雨要下大了。”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默默地抹了一下头发,然后慢慢往山下走去。两只泪眼
一晃,在松明火把下发出光亮。
“走错了!下山走那边!”有人提醒她。
她呆了一下,木头似的转过身子,顺从地照人家吩咐的路线走。
“走中间呀,路边有狗公刺挂裤脚!”
她又木然地往路中间靠了一步。
回到她家,已是深夜。由于长顺的邀请,我进去坐了一阵。说来惭愧,
来队一个多月,我事情多,还没到他家来过。一进门我的血仿佛凝结了,腿
也像被什么钉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两间矮小的房子,床
是用土砖门板搭成的,低垂的破蚊帐被烟火熏成黑色,因为灶就挤在床前不
远。被絮破旧而没包被单。土砖架上木板就是饭桌。灶上一盏用墨水瓶做成
的、没有玻璃罩的油灯,晃着昏黄的火苗。隔壁,传来一股难闻的气味。长
顺的娘在那边连声咳嗽,这个不怎么令人喜欢的老太婆,还高一声低一声数
落着媳妇的不是,听口气好像是埋怨月兰身体不好,又不会持家,治病亏了
账,搞得屋里穷,孙伢子读书没着落。老太婆后悔不该收这个“药罐子”媳
妇……
但在一片混乱中,像一道电光闪过,我看到墙上十几张陈旧的奖状。我
忙把六叔拖到一边悄悄问:“他们是优秀社员吗?”
“当然啦!”六叔喷了口烟,“长顺做事一个当两个。月兰也是个好妹
子。只说那年春插,队上牛乏了力睡在田里,她一气拿出十几个鸡蛋、两斤
甜酒把牛吃,还硬不要钱……”
我的心颤了一下,简直无法把这个献鸡蛋的月兰和那个放鸡下田的月兰
的形象统一起来。
“张同志,请坐。”长顺苦笑着把一条粗糙的铡刀凳抽到我跟前,“实
在对不起,椅子都没一张……”
“怎么没椅子?”
“我,我……”他不好怎么说。
六叔磕磕烟袋,插嘴道:“他家是个大超支户!去年刮起一阵风要还清
超支,他就把柜子、床、椅子都作价还到大队上去啦!”
“劳力这么强,怎么会超支?”
长顺又露出一丝苦笑。
又是六叔插嘴帮他说清:原来去年月兰长瘤子得了一场大病,缺工不算
,请郎中、住医院一下开销五百块。要是往常这也不算什么,可这几年队上
连年减产,搞得很乱。今年奉命修个大水库,明年又奉命废掉水库造“小平
原”;只能插单季稻的硬要插双季;多种经营的门路也被堵死。
P7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