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
本书的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交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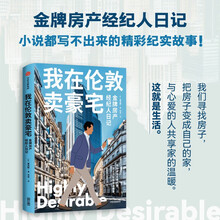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决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踌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