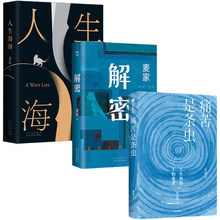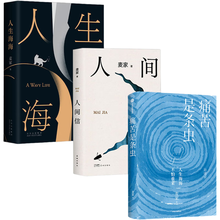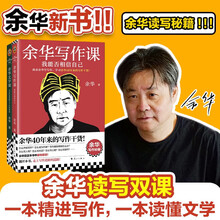阑尾和阑尾炎
在我们最后的晚餐上,朱爱笛提到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 我说过,作为一个背叛家庭和爱情的犹大,朱爱笛没有资格谈论 这件事情。但我没有把它点破。不过,我非常清楚,朱爱笛那样 说的目的还是很明确,而且是善意的。她是为了劝告王一杰,一 定要抓住现代化提供的机会,以免落得焦仲卿那种自挂东南枝的 下场,才说到了焦刘二人的悲剧。
朱爱笛的好意我当然能够理会。即使她把我给蹬了,我对她 也有那么一点不大不小的意见,觉得她把誓言当儿戏,但这并不 能表明人家是个完全忘恩负义之人,也不能证明我一点错都没有。 王一杰没本事当官发财,甚至连一个伪学者都没本事混上,这在 今天就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人家朱爱笛走入新爱情没几天,就 给我打电话,通报辛追可以当零食的消息,就是人家朱爱笛有良 心、讲义气的明证。至少我愿意强迫自己这样看待问题。在和辛 追互赠照片和讨论过“认识”(Vada)的涵义之后,我对朱爱笛的 感激就更加强烈了,也对她起了故园之情。
没过几天,朱爱笛又打来电话,询问我和辛追的最新情况。 “是不是已经睡在了一起?零食还吃得有滋有味吧?”她在电话那 头说,“时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即使按照你走动缓慢的生物钟, 估计也该下手了。”我告诉朱爱笛,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不要 把什么交往都朝力必多身上扯,好不好?再说了,当年的三个月, 你还不是觉得快了?朱爱笛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听上去幸福之极:“网络交流嘛,又不比从前。你这个人就是面浅,宁愿自己憋着,也不向人讨食。其实那有什么呀。”最后她当机立断,“如果你不好意思向人家吐口,我愿意冒充你上网跟那个辛追说。把口令告诉我就行了。”
我问朱爱笛,你管闲事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一些。就算朕有点释放力必多的想法,也用不着太监着急。朱爱笛在那头笑得越发来劲:“我管闲事,还不是怕你去自挂东南枝。”我气得浑身冒泡,大声质问她:你有什么办法吐口?你凭什么那样自信?就凭你老牛啃了一把嫩草?说完这话,我马上就后悔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想啃一把水灵灵的嫩草,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前妻那样有志者事竟成。
朱爱笛果然大笑起来,完全不顾及我对她明显的敌意:“凭什么?就凭我代你向那个老娘们发誓嘛。你连这个办法都不懂,是不是真的退化了。当年你不就是这样把我给摆平的吗?”尽管她说的不全是实话,但我自知理亏,只好忍气吞声,沮丧地告诉她:誓我是发过的,如今也好端端地摆在那里,我可从来就没有违背过。朱爱笛闻听之下,大喝一声“呸”!然后才说:别的都不计较了,你没有退化那就再好不过。去!你现在就去向那个老娘们发誓,反正有那么多夏雨雪天地裂一寸相思一寸灰之类的诗句,还都是现成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听了她一番教诲,我默然良久,觉得道不同不相与谋。就自作主张挂了机。朱爱笛见我胆敢擅自做主,不听她的指示,又怒气冲冲把电话给打了过来。但我懒得理她,任凭电话铃声像炸雷一样在空旷的屋子里暴响。我神神道道,居然又想起了最后一顿晚餐上的“自挂东南枝”。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