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指走到了马绪安跟前,六指一瞄见马绪安就向他跟前走。他看也没有看马绪安就像刚才踢周雨言一样踢了马绪安一脚,六指的脚还没收回去,马绪安就趴倒在坚硬如铁的棉花地里了,他大概预料到六指会很利索地踢他一脚的,他有了防备,才不至于使嘴脸在地上受伤。马绪安慢慢地站起来,他盯了六指一眼。马绪安的眼神里含有愤恨和嘲笑,眼角里睇出的那种蔑视使六指恼羞成怒。
六指咬着牙说:“你看?你再看我一眼,我就把你的贼眼珠抠了。”
马绪安那有限的傲慢经不住六指的恐吓,他低下了头。他还是惧怕,惧怕六指抠了他的眼珠。六指的手是很毒的,这一点,马绪安最清楚。他要看一看六指终究会有什么下场,他似乎就是为了这个简单的目的挣扎在人世上的。六指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他的父亲刘长庆的血,六指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马绪安的血,这个儿子一点儿也不像他,只有那份霸道和年轻时的他很相
近。
马绪安双手拄着光滑的镢头把儿,他眯着眼看着名分上是刘长庆的儿子实际上是自己的血脉的六指从他混浊的眼神中逸出去。儿子的背影幻化为一个凄凉的坟堆,其实,坟堆就在他的身旁。他恍然看见坟堆中那个不太精致的盒子里有副骷髅,骷髅苏醒着丰满着,丰满了一个硕壮的年轻女人。女人说,儿子踢你,你怎么就不吭一声?马绪安说,我现在不是他的父亲,是他的敌人。女人说,你应当给他说清,你不是他的敌人,是他的爹。马绪安凄苦地笑了:我是六指的爹?闹娃,这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女人说,我有了。
女人挑亮了烟灯,她的嘴噙着烟枪贪婪地吸了两口。
有了好。马绪安若无其事地说。
长庆回来咋办呀?女人按撩不住的不只是慌恐,她明显地流露着内疚和自责。
马绪安从枕头边抓过来盒子枪看了看乌黑的枪身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浮尘,又放在了原地方:让这支抢和长庆说话吧。
女人丢下了烟枪用双腿缠住了马绪安。
保长马绪安和刘长庆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女人闹娃在这条土炕上整整滚了六年。卖过三次壮丁的刘长庆在中条山和日本人作战时伤了一条胳膊之后回到了松陵村。回来了又能怎么样?明知六指是马绪安的种又能怎么样?一家五口人要靠掏马绪安的腰包生活,有闹娃那漂亮的脸蛋和肥硕的尻蛋子就什么都有了;用女人本身去换取粮食衣物钞票并不是闹娃的发明只是她的继承,就像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和债务一样,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刘长庆躲进雍山里长年不回家,他将夫妻的名义留给自己而将闹娃肥壮的肉身子留给马绪安留给不可缺少的粮食以及钱和物。六指在一个傍晚忽然明白了村里人骂他你是靠你娘的骚X养大的那句脏话的内涵之后,他第一次将前来娘屋里过夜的马绪安关在了院门外边。闹娃给马绪安拉开了门闩,马绪安看了看不谙世事的六指说这娃一点儿也不知道孝顺。在一个淫雨连绵的日子里六指对闹娃说,我长大后就把他杀了。年幼的六指将牙咬得如同炒豆子一般响,尖刻的响声使闹娃齿寒心颤。闹娃怆然地说娃呀,活人要靠粮食,人是粮食吃大的,只有粮食靠得住其它都是靠不住的,你杀了他就等于杀了你的那一份粮食。她的话六指无动于衷,他脸上敷着的那层嫩嫩的杀气同他一起成长,他吃饱了肚子就对粮食没有多少醒悟,他除了需要粮食之外似乎还需要其它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杀了马绪安他才觉得心绪能够平静。
不动声色的阴影像乌鸦的翅膀一般在我的头顶不停地扇动着,我想极力摆脱它总是摆脱不了。阴影老是尾随着我,将我紧逼。其实,我没有必要摆脱更没有必要选择,还选择什么?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我真不明白,哥,、你为什么要老远老远地跑到雍山脚下?难道没有更好的去处?我说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父亲说不一样,父亲说跳到大口井里去是整治人,要捞上来多么不容易,父亲从宋村回来后就这么说,父亲说宋三的儿子跳进大口井里了,井水足足有八丈深;宋三的儿子大概在身上绑着石头,大概一头下去就扎进青泥中了,打捞了两天,还没有捞上来。大口井的口径至少有五丈,站在井口边看一眼就头眩目晕。我一只手紧紧地拉住雨梅从井边绕过去。我老远看见野菊花遮掩着的井口就对雨梅说,小心前边有井。雨梅说井在哪里?我用手一指,我说就是蒿草丛遮着的那个地方。井口虽然被伪蔽着,我还是能嗅出井的气味和它的可怕。雨梅不以为然,她挣脱了我,她说你就那么怕井?二哥。我说我就是害怕井。我说你不怕井?雨梅。雨梅说她不怕,雨梅说有二哥在身边,她是啥也不怕的。不要害怕,既然决定了还害怕什么?
见了雨梅怎么说呢?就直接地说,问她愿意不愿意,问她害怕不害怕。不行,那样不行,也许她不愿意的,她牵挂着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对自己她早已不在乎了。算了吧,一句话也不说,等吃饭的时候再下手。走吧好妹妹,和我一块儿离开,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这个世界。你走不动?雨梅说二哥我走不动了。我说走不动了就歇一会儿吧。我和雨梅将山柴捆子放在了盘山路上的一块平坦处。这条路从雍山顶上挂下来,向上看,像父亲的腰带似的,窄巴巴的路上到处是搓脚石,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路旁的野花卷起了枯萎的叶子,枝杆卜勉强地顶着衰败的小花,我记得野花的香味,在它们最富有的季节,花的香气会像清澈的水一样漫流。现在,它们算是活到了最凄楚的时候。没有开不败的花。雨梅放下山柴捆子抱紧了衣服,冷风一吹,汗湿的脊背就很冰凉了,她抱着膀子说二哥你看,现在的天多好看。一脉雍山给天际染上了一道冷峻的黑边,高远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显得很纯粹,太阳的光线仿佛上足了釉彩的瓷器。我说,这天气就是好。雨梅说,二哥,将来我画画儿你写文章,我的这幅画儿就叫蓝天,怎么样?我说,还是叫挂在蓝天上的饥饿吧。我们得到的饥饿是太多了,我们的活着只是为了塞饱肚子。雨梅说二哥,我饿得不行了。我说,我也饿了。雨梅说,二哥,我给你做饭去,等吃完饭你再回去吧。等雨梅将饭碗端进来之后我就把她支使出去然后将药分别放进两个饭碗中。那种药没有什么难闻的气味,她肯定闻不出来的。,母亲说,你吃了饭再去雨梅家里。我说我到雨梅家里再吃。母亲说,她们家里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负担。小凤接上了话,小凤说,雨梅和我娘会叫他吃好的。见了小风的娘我一定得像往常一样叫她丈母娘的。我的丈母娘就是雨梅的婆婆,换亲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捣乱了。不过,我得感谢小凤的,如果不是小凤搭上话,母亲肯定不会叫我吃饭前去雨梅家的。
天蒙蒙亮,周雨言就起床了p他晚上无论睡得多晚,按时起床的习惯不改。周雨言洗刷完毕打扫房间里外的时候才发现,他的门口有一条手绢,他拾起来看了看,这是一条洗得很干净的但已很旧的花手绢。是谁将手绢丢在了他的门口?晚上临睡时他怎么也没有发现?他敢肯定,这条手绢不是秋月的,秋月已有三天没来他这儿了,秋月使用的手绢他认得出来。周雨言首先想到的是秋月,他未曾想到他的妻子会深夜潜入乡政府,会将手绢遗落在他的房子门口。手绢确实是吴小凤的,站在凳子上的吴小凤捕捉到房间里的模糊之后以为她的眼睛出了什么毛病就掏出来手绢去揩擦,她越擦越看不清,慌乱之中,手绢没有送进衣服口袋落在了地下。吴小凤没有意识到她将手绢掉在了周雨言的房子门口。
吃毕早饭,周雨言正坐在房间里想那条花手绢的事,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一个人在呼喊什么就走出了房间,只见前院里有几个乡机关的干事围拢在一块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挤到跟前去一看,有些吃惊。一个瘦骨嶙峋胡子雪白的老头子高举着一张状子直直地跪在乡政府门前嘴里喊着冤枉。他问民政干事是怎么回事,民政于事嘻嘻一笑,说,也怪这老汉多事,老汉的儿媳妇和村上的牛支书睡觉,儿子也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这事偏偏让老汉撞上了。老汉大呼小叫把牛支书弄得下不了台。事过半年,老汉申请宅基地,乡政府倒是给老汉批了一院宅基地。牛支书把老汉名下的宅基地给了他弟弟,老汉上告了多次没有人管,乡政府也管不了。民政干事吸了吸鼻子说,连县上的干部也不愿意得罪牛支书,乡政府敢管?牛支书是市政协委员,农民企业家,睡几个女人算个*事!周雨言说,这怎么行呢?牛支书是党的干部,咋能像土匪一样?民政干事说,这咋不行?牛支书答应下一次给老汉另外批宅基地,不是不给他。周雨言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这不是明明哄老汉吗?民政干事说,没三年五年,这老汉休想再批一院宅基地。周雨言要去将老汉扶起来,乡长黄祥民在他的门口呼喊:“周雨言,你来一下。”
一进黄乡长的房子,黄祥民就说:“有什么看头?告状的事隔几天就有,你能看得完?你是不是看那老汉可怜?比他可怜的农民多的是。”周雨言以为黄乡长是将他叫来专门听他发牢骚的,就坐下来听他说。“这老汉的事县信访局不管,纪检委不管,民政局不管,一句话推给了乡政府,他们尽装好人。和老百姓直接接火的事,坑害老百姓的事就推给了我们?口口声声有政策,他们咋不直接去执行?催粮要款,刮宫引产,哪一样事不要乡上的干部去管?”黄祥民看了一眼周雨言仿佛觉得他把发牢骚的对象搞错了,他不是叫周雨言来听他发牢骚的?他不自然地挠了挠头发,从桌子上拿出来一份材料,问周雨言:“材料上面的数字怎么没写上去?”不是周雨言粗心.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写,他说:“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和年终总结上的数字出入太大,比如说粮食总产,乡镇企业总产值都比年终总结上写的多得多。”黄祥民说:“你就按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写,这是乡党委研究过的。我们在数字上已吃了不少亏,去年上报数字的时候我就给办公室打过招呼,叫他们去其它乡镇打听一下,其它乡镇人均收入报一千元咱就报一千零一元,粮食产量也一样,也得比其它乡镇略高一点才是,办公室的老马不听我的话,如实上报了。结果,年终兑现,其它乡镇的干部都有奖励,惟独咱们没有。是不是咱们的工作落后了?不是的,是咱们的数字落后了。这一次评文明乡镇,数字一定要写上去:上面不会有人来调查的,他们不过是看看材料。”黄祥民在周雨言的肩膀上拍了拍,他说:“周雨言,只要你的材料写得好,评文明乡就有了九分的把握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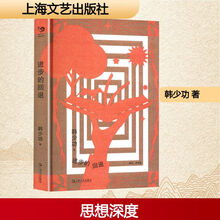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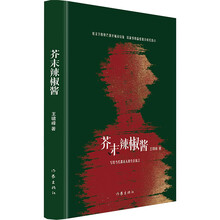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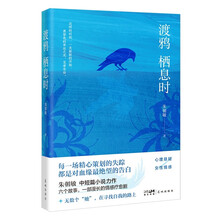
关于“九头鸟”,《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曾写道:“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正字通》云九头鸟:“状如鸺嚇,大者广翼丈许,昼盲夜濛,见火光辄堕。”宋梅尧臣《古风》诗:“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 自从狗啮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鸺嗽。”但是后来,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提起湖北籍的人氏,人们会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其意,是湖北
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自然不是对手。湖北是九省通衢,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在人们的印象中,湖北人会经商,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无商不奸,与湖北人打交道,小心吃了亏。所以,九头鸟之于湖北人,实际上是具有一定贬意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复合型人才吗?而“广翼丈许”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不过,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如12万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来冠之以“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后来,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经过商量,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我们准备像“跨世纪文丛”一样,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总题用“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小说。当然,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不能仅看篇幅长短,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我们既重视题材的多样性,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否则,我们这套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
我们十分明白,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的,这套小说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像我社的“跨世纪文丛”一样,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