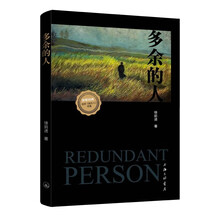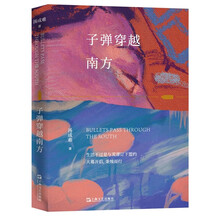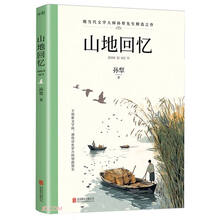方梦渔点头说:“也好!”遂就跟她并肩过了马路,往西去走,斜斜脸儿又看看她,问说:“魏小姐你现在还做着别的事吗?”<br> 魏芳霞摇摇头说:“也没有别的事,家里的事也就够忙的啦!”<br> 方梦渔进一步地问说:“魏小姐没有再出台演唱的意思吗?”他这句话却没得到答复,等于是碰了个钉子,他只好闲扯,说:“其实我也没有听过绮艳花的戏,不过今天这么一看,她的朋友可真不少呀!朋友多了自然能够帮助事业的成功,也可以帮助艺术的增进,不过我总觉着……”<br> 魏芳霞却斜斜脸说:“您可别说她什么,她是我的表姊。”说完了这话,她又一笑。<br> 方梦渔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笑笑又说:“我可还得说说,我对于戏剧,虽然不懂,可也是一个爱好者。我对于坤伶仅仅认识你们表姊妹两人。不过我总觉得女伶是应当有点学<br> 生气,至少应当有闺秀气。”<br> 魏芳霞笑笑说:“我可不算是女伶了,我早没就有那种资格了,什么学生气,闺秀气,我想我都是一点也没有。我就是这样,我不能说绮艳花不好,可是她现在唱红啦,朋友多,人缘又好,叫人请到上海去,我!我却一点也不羡慕她!”<br> 方梦渔说:“不过既然唱戏,就应当唱红,就如作一件事或研究一门学问,艺术,是应当让它成功。”<br> 魏芳霞不言语,依旧同着方梦渔往西走。<br> 方梦渔又随走随说:“我劝魏小姐,也不应当灰心,学武生虽然现在不走运,可是你应当也改学旦。”<br> 魏芳霞又半天没言语,走进了“西河沿”那条胡同,她才悲哀地说:“改学旦?可不是容易的事儿!”<br> 方梦渔摇头说:“不!你很有天才,我看得出来,你若是改学旦,一定能够超过绮艳花。”<br> 魏芳霞笑一笑,说:“得啦!您别说了!那有当面捧人的?可是……”她的容态又变为忧郁,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br> 方梦渔问:“难道还有什么困难吗?”<br> 魏芳霞说:“得啦!您别再说啦!我就告诉您吧,要改我早就改啦!总是改不了,您也不必问是为什么原因,现在要不是绮艳花是我的表姊,我连唱戏的事,是永远一句也不提!”<br> 方梦渔说:“这可就奇怪了!莫非……”他不能再往下问。<br> 魏芳霞赶紧说:“您还别疑惑我因为唱戏,有过什么伤心的事……”<br> 方梦渔说:“我觉得一个唱过戏的,并且不是不聪明,不努力的人,只因为时势的变迁,潮流的演进,而不能再唱了,受了淘汰了,这可也算是件伤心的事!”<br> 魏芳霞又斜脸来看他,眼睛迎着路灯,显出来荧荧欲泪的样子,她勉强作笑,说:“我可真头一回遇见您这样的人,人家不伤心,您还偏要勾人的伤心……”<br> 方梦渔也不能再说什么了,不过心里总有些不平,觉着像她这样美丽聪明而且又不是没有唱过戏,倘或能够合着剧界的趋势,改学青衣花旦,那准保压下去绮艳花,到上海去出演?还许出外洋呢!一定能够成为最有名的一位坤旦,只是她不肯这样作,也不知是有什么原因,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br> 这是一个晴和的天气,空中飘荡着柳棉,方梦渔换上洋服,把皮鞋还擦了擦,赶忙发完了稿子,才不过上午十一点多钟,他就去了。<br> 小碧芬结婚的礼堂设在宴华楼,这是当然的,因为今天的新郎,就是这家规模豪华的中餐馆的主人。方梦渔来到这里一看,男客女客已经不少,大多是金融界的。商界的和政界的,也有新闻界的。可见小碧芬的新郎交际甚广,他是一个大胖子,年纪有四十多了,穿着大礼服,人是十分和蔼,有新闻界的朋友给方梦渔介绍,这位新郎伸着胖手来跟他紧紧地握着,说:“方先生我是久仰啦!碧芬几乎天天跟我说,怎么?尊夫人今天不来吗?”方梦渔一听,小碧芬跟他天天说,倒许是真的,可是他一定没有一次是听明白了,要不,怎会以为他是有夫人的人呢?可是这时也不必辩解,他只说:“没有!没有了新郎请他落座,就又招呼别的客人去了。客人<br> 是不断的来,女客仿佛比男客更多,可是,不用说魏芳霞没有来,连绮艳花也没有看见。<br> 这倒不必多疑芳霞和绮艳花,今天就是来,也一定跟随新娘一块儿来,她们原本是坤伶中的鼎足三杰。然而完了,都完了,小碧芬今天就“名花有主”,绮艳花自上海是“锻羽而归”,芳霞是“佳人已属沙吒利!”<br> 他真难受,坐在这舒适的沙发上,竟像坐针毡一样,东瞧瞧,西望望,加倍地感慨丛生,这个地方还不就是自己作东道,为魏芳霞大请客的那地方吗?这才多少日,事情竟变化得这样迅速、剧烈,叫人想不到。跟女人接近总是危险的;然而男子总难免要与女人接近,不然,今天这里为什么要结婚?这些个女客,有的是已经结了婚,有的是大概不久也得结婚,结婚是形式,事实就是男女接近。我跟魏芬霞稍微接近了一点,人家就说我们要结婚,结果她叫贾大哥儿抢了去。贾大哥儿虽结过婚,可是另外还要跟她以不结婚而“结婚”,她也就这么马马虎虎的,没结婚也等于是跟人结了婚。“结婚”,这结婚之中有多少骗局,多少暴虐,男人造成罪恶,女人走人堕落。他这样地想,气得不住地喘气,他简直是要发疯了。<br> 走出了汉中府的南关,横在眼前的便是汉水,这道江发源于陕西宁羌县北蟠家山,东流纳沔、褒诸水直到汉中府,再纡回东流,流人湖北省,沿途纳集诸水,顺着大洪山的西麓,至汉阴县流人长江,这是一道大江。陕南出产的生丝、桐油、紫阳茶叶等等,都由汉中府装船运往南方。这里,白昼是风帆往来,夜晚是樯桅林立,当下,小银枪雷俊保,车一到了江岸,就急呼渡船,虽然现在正是深夜,船家都已睡眠,舱中很少有灯火,但天上的星光却又多又亮,照着下面黑荡荡的江水,风也在江上呼呼吹着,到底小银枪令赶车的去叫醒了一只很大的预备载货的船上的人,人家这时候谁还愿意渡人呀,可是小银枪在岸上大喊:“我是霄次太爷,有要紧的事,快把我连车都渡过去。”“雷次太爷”这四个字,令人听了害怕,镇台的内亲,又是一方的财主,武艺还高,“家将”无数,谁敢惹他,当时这船上的几个人,睡眼矇眬慌忙出了舱,连话也不敢多说,就往岸上搭跳板,小银枪坐在车上还不下去,赶车的“忽隆”一声,连骡子带车,就都赶到这只大船上了。小银枪已知身后有马追来,便吩咐他的车夫和众船夫说:“你们问问北边来的是谁的马,是我家里的人才准上船。”他还以为是他的家将,割风刀胡诩,穿云箭鲁腾,展月钩罗岳,断水剑姚忠,那四个人来了呢,赶车的和船夫们都向岸上大声地说:“是谁,是谁,从那里来的?”可是“忽喇”一声两匹马追到了,一句话也不说,原来是蕙秋与韦梁,一看见那辆带着灯笼的车在船上了,他们就知道没有错,所以双马前后也越上了船,蕙秋拧枪向着车棚子就扎,“通”的一声,将车后棚扎了一个大洞、船夫、车夫,全都吓得惊喊着逃躲,蕙秋便说:“雷俊保你出来吧!我只问你,我爸爸在那儿,李春棠在那儿……”车上的小银枪早就知道出了“差子”啦,来了敌人啦,他已经由车钻出,直跳到船板,手中拿着他的“银枪,”——他这枪原是上下两个枪人,小间有“笋子,”接在一处便是一杆,可以如赵子龙一样的冲锋陷阵。但分开了便是两只,既是携带便利,又可当作短兵器用,此时弛以两只短枪探向前来,一对枪头映着星月之光闪烁发亮,他高喊着问:“来的是谁,啊呀,来的原是假袁小姐,找还以为至早你也得等到明天夜里,才或者到我家里去找我,没想到你比我的性子还急。”蕙秋已经下了马,突的又一戟扎来,雷俊保用一双短枪交叉着去架,他又说:“别这样!咱们也算是亲戚。”蕙秋却怒着说:“谁跟你是亲戚?快说,我爸爸在那里?”韦梁也下了马,自侧舞双刀,向着雷俊保来削,雷俊保惊讶着,急以半截枪挡蕙秋,另一半截枪来敌韦梁,急问着说:“你是谁?”韦梁说:“我叫赛潘安,你大概还不认识我,小辈,你快说出来吧!反正我已经看见了,双钩小姐是前天才来到的,我见她独自进城找过你,那日傍晚时,她过江骑着马往东南方向去了。”小银枪雷俊保傲然地说:“很对,你们为什么不快过江往东南方去找呢,反来问我,告诉你们,我雷某并不怕你们,我这一杆银枪……”说时“吧”的一声将两只短枪,接在一处,立时就变成了一杆长枪,先抖了一个凤凰乱点头,蕙秋又探戟猛刺,他却退到舱门,以枪按住了蕙秋的戟,他又冷笑说:“你们不是要问我吗,先听我说几句<br> 话,我是四川小峨嵋云老娘娘的弟子,你知道云老娘娘与她的女儿双钩小姐李春棠……”蕙秋发怒地说:“你快说,不要费这些话!我早知道双钩小姐就是李春棠。”雷俊保接着说:“她<br> 们母女与唐立冲有不共戴天之仇。”蕙秋问:“为什么?”雷俊保说:“连我也不知道,不过要想擒拿铁面温侯唐立冲,却也不易,她们曾屡次托过我,并命令过我,但我与姓唐的不相识,她们又叫我去转托袁镇台……”蕙秋赶紧又问:“袁镇台跟我爸爸又有什么仇?”霄俊保说:“这我倒知道,听说他们早先同在福康安的麾下,军伍之中,唐立冲的蛟龙戟就很出名,袁镇台的大刀也耍得很好,两人都气胜,谁也看不起谁,就在剑门山下比过武,结果袁镇台的左膀受伤,可是他后来作了总镇,他的记性不好,有时想报那一戟之仇,有时他可又忘了,再说你看,连章广贵在秦岭中害死他的亲女,他至今仍然不晓得,凭他那里还能捉得住你父亲,不过他倒有时就骂,章广贵是他的多年亲随,所以很晓得此事……”蕙秋发躁地说:“你快说,我父亲到底在什么地方?”雷俊保说:“你父亲确是被李春棠亲手所擒,不过出了秦岭,曾经有官人帮助,那也因为双钩小姐本来有名,官人对她,又敬又畏,与袁总镇不相干,后来由官人帮助,就把你的父亲送到一个地方去了……”蕙秋拧戟进一步地又来问:“现在什么地方,你快说厂雷俊保说:“就在东南……”冷笑了笑又说: “我此刻也是想看看去,因为,我对这件事,也是有点儿生气,双钩小姐前天回来见我,说是仇人唐立冲已被她生擒住了,但是,我恼她的就是她并没有把你为救父紧紧随后追来的事情,说出半个字,直到今晚,我听说镇台的小姐从北京来啦,我想一个人那能死又重生,我觉着奇怪,才赶紧去看,去时正见你在院中练戟,我见你的武艺那样好,才又觉出必有事情,后来从你亲口中说出来你是铁面温侯的亲女,并在秦岭与双钩小姐曾经厮杀,我就太觉着心里不痛快了,其实你们的事情我不管也行,只是我独恨双钩小姐,她为什么不把你这样的一位美貌无双,武艺超群的姑娘先告诉我,难道她是有点儿吃醋。”韦梁此时跳起来用双刀就砍,蕙秋更狠狠地拧戟来扎,雷俊保却抖银枪敌住了二人,且战还且讲,又说:双钩小姐是我的情人,她不告诉我你快来到了,许是怕我把你看上,因为你比她长得更漂亮,我这个人又是一个多情种子,最倾心于一些美貌的姑娘,我刚才陪着袁总镇玩益智图,我就想了半天,结果决定急速去找她,一来问她为什么不先告诉我说,二来叫她得多加防备,我也想到不久你们必能找了去,所以我先命人去叫我的家将,以便去帮助她,可是你们要叫我不帮双钩小姐,这也行,唐姑娘,你得亲口求求我,我能为你们解合,你可也得答应跟我好……”他的枪法很熟,就在这船板上,地方虽不宽,碍事的东西又多,但是他竟能够施展得开,枪舞如飞,“凤点头,”“梨花摆头,”“砍月,”“抽丝,”“骑龙,”“钻塔,”招数百出,舞起来如惊涛骇浪,鬼神不测,上下难防。但蕙秋的一杆戟,也不稍让,戟如疾风,迎枪转枪,有隙便进;韦梁的双刀也闪闪的在旁助威,渐渐都要把他雷俊保逼到船舱里边去了。此时,韦梁就看见北岸上有四匹马飞驰而来了,猜首必是雷俊保手下的人,如果来到,可就更不容易制他们了,弄得自己的这边反倒人少了,他们那边,反倒人多势众,于是韦梁便叫蕙秋独自敌住雷俊保,他却持双刀去逼那几个船夫,喊着说:“快开船!快开船!”几个船夫早就吓得昏了,藏躲到船边,都快掉在水里了,缆已经解下来了,但几只长大的篙,找了半天,才找着,船身不住地晃晃摇摇,骡子直嘶叫,棚儿车也要滚下江去,赶车的人藏在车底,那只灯笼也灭了。韦梁又大声的喊着,“快开船……”这只大船才由几个船夫一齐用力,下篙,转舵——倒是没有扯帆,就向着黑水茫茫的江心驶去。船在向前驶着,雷俊保已经退到船里,可仍将银枪探出了舱门,拚死力与蕙秋厮杀,越杀越急。这时岸上的四匹马,雷家的“家将”割风刀胡诩等四人已经赶到了江边,但是船已走了,他们望着船,听着那一片杀声,只是干着急,江边虽还有不少只船,可是此时都把舱门闭得很紧,就是已经被外面的声音所惊醒了的人,可有谁又敢出来管闲事,割风刀胡诩等人就跟强盗一般,他们跳上一只装茶<br> 叶的较小的船,踹开了船舱,持刀剑和护手钩威吓着船上的几个人,自称他们是“镇台衙门的官人,”今急速开船,去追前边的那只大船,他们并将四匹马全都牵到这只船上了。于是以刀割缆,船只自动,穿云箭鲁腾,展月钩罗岳,他们先自己使起篙来,船只就向前疾进,冲破了江波,东倒西斜,他们也不管这只船稳不稳,割风刀胡诩仍大呼着:“快迫,快进!”究竟前边的那大船行得迟缓,霎时间,就快要被这只船追上了,穿云箭鲁腾踹了一个船夫一脚,说:“给你篙,你快拨!”他腾出手来,就到马旁摘弓取箭,“飕”的一支箭射去,然而“吧”被那只船上的赛潘安用刀把箭撞回来了,鲁腾挽弓又要射去第二支,断水剑姚忠着急得跳起来说:“别再射啦,次太爷就在那船上,你射着了他可怎么好。”罗岳又说:“还得快追!”船更晃晃摇摇地疾驶,那边赛潘安站在船尾高声说, “谁敢来,谁不怕死谁就来!”江水愈黑也似流得更急,江心的风也更猛,天上的星光月光都模糊了,刀光、枪影,依然闪闪烁烁如几股<br> 白气,忽然两船即将互相靠住,断水剑姚忠喊一声:“我来了,你们那个敢欺负我家的次太爷。”他将身一耸,就要由小船跳上大船,但还没有跳上去,就被赛潘安韦梁双刀搂头砍下,“口克,”的一声,姚忠惨叫,扔剑,还想用手扳住船尾,但是扳不及,身子“噗通”一声,就落下江里去了,将水溅起了多高,罗岳大声嚷:“不好,姚忠死了!”胡诩仍然挥刀大喊:“替他去报仇!”于是船仍向前迫,“哐”的一声,,这船的船头,撞着那船的船尾,几乎倒把这只船撞翻了,胡诩抡刀,鲁腾扔了弓去提斧,二人都十分勇敢,齐向大船上去跳,竟被他们跳上了那只船,韦梁也奋勇来与他们厮杀,同时蕙秋还以为这时不定是有多少人都来帮助雷俊保,她恐怕韦梁吃亏,就暂时舍弃了雷俊保,而回身拧戟来敌这二人,她的画戟刺处,鲁腾又<br> “吓通”一下坠入了水。胡诩一面胡抡刀,一面又大声叫,说:“可坏啦,次太爷,鲁腾跟姚忠,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可全都死啦……”此时,雷俊保才由舱中钻出头来,又晃摇着他的银<br> 枪,扯开了嗓子急喊:“算了,算了吧,我认输啦,唐小姐,跟那位朋友!本来咱们都没有仇,现在我带着你们去找李春棠,就去救出铁面温侯,还不行吗。请你们先住手……”蕙秋听了这话,才收住了戟势,转身又向雷俊保,用戟指着说:“你可准带着我们去。”韦梁也举双刀说:“不然还是杀了你!”雷俊保却把银枪向船板上一扔,又喘息,又叹气,说:“我真没想到,横行陕南六七年,今夜竟在你们的手里栽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