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婆惊愕地看着这个不大开口讲话的女人,几十年了,她还是第一次听见她开口说话。这个从来不在外人面前开口的女人,现在嘴巴快乐地抖动着,一脸郑重地讲述了她刚才所做的梦。当她说到远天那一片红光的时候,产婆顺着她的声音向窗外望去,正午的天空里竟然真的是一片通红,太阳如同燃烧了一般。她的口音让产婆觉得像做梦一样的动听,软软的,浓浓的,咿咿呀呀然而又是一字一句的,像炒豆子般清脆。村里人没有说错,她是个南方的蛮子。她说完了,突然有些窘迫,好像自己也突然被刚才说出来的话语震住了。她的眼睛祈求地望着产婆,自言自语地说,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啊?我不该透露神的旨意的,你不要说出去好吗?
产婆惊慌地点了点头,她刚刚为孩子接生出了一身透汗,现在她的脊背却是一阵一阵的发凉。她是退着从王家出去的,在门口绊了一跤。她给村里娃娃接了几十年的生,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产婆绊了一跤,她把王家儿子给他装的红鸡蛋撒落得满屋子滚动。她顾不得去捡,也许她根本不敢去捡,她像那些鸡蛋一样从王家的院门里滚了出去。接着她好像是着了魔一样,她再也停不下来,她一下子滚过了整个村子,把每个角落都滚遍了。
这个该死的产婆子啊,王家的奶奶怎么可以信任她的承诺,她把王家孩子的事情比风都快地在村里吹了一遍。末了她还说,我是绊了一跤,骇得路都不会走了,那些鸡蛋个个倒像是长了腿一样。我接了半辈子的孩子,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村里有许多人都是不怎么相信产婆子的鬼话的,正像他们不怎么相信媒婆子的话一样。大队里的干部,还有大队里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受过党的教育的,而且在剿匪反霸和肃反镇反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变得唯物起来。但是这些话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坑洼不平的村街上流传起来。党员干部忧心忡忡地到支书这里反映情况。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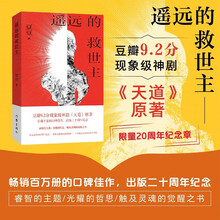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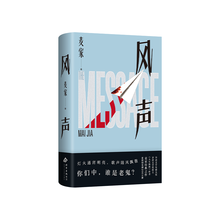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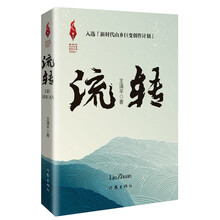
——王干(《长恨歌》责任编辑)
邵丽把平步青云,一呼百应的官员下放到“人”的层次上去观察,心平气和地看那些去掉权力光环的人,这样,她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看到人性背后的矛盾和尴尬。
王祈隆生活在秩序中,生活质量却在秩序之外。
——脚印(《尘埃落定》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