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丁太本是个富足商人家的千金,她聪明,美丽。但不长时间之内,她的母亲带着全部家当与人私奔了,她的父亲则死无葬身之地。她只有放弃自己的中学学业,去姑母家挣钱还债。然后,尽快找了个婆家。可二儿子尚未出世,丈夫就出事了。那时,丁太只有24岁。但她为了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一直守寡。为了孩子长大成人,丁太什么都干,甚至当街捡起了垃圾。如今,两个儿子都成家,又有了孙子与重孙,可谓四世同堂。丁太理所当然、毫无怨言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拉扯大,主动将所有的家务承担了下来,并且以此为乐。但丁太逐渐地发现,自己由家庭的支柱及中心,慢慢地成了累赘。家里人从儿子、媳妇到孙子、孙媳妇,都在心里认定,没了丁太,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而且,这种想法变本加厉的变成了彼此之间的争斗和一次又一次共同的阴谋。终于有一天,丁太气之不过,喝下了“敌敌畏”。大家心照不宣地在心里庆贺,无比地轻松。不曾想,做事干净利落的丁太此际却像在故意拖延。医院要一天天地呆下去,大家不得不从没了丁太的大解放的心态中无奈的沉降下来。从即将面临的医药费到以后的抚养问题,让丁家兄弟越想越远。最后,两人将戏一边导着,一边演着,共同推向了高潮。未曾瞑目的丁太被他们推往了火葬场。火葬场停了电。隔天,当家里正在豪华的操办丧事的时候,丁太终于能喊出声了。所有被结构好的故事穿帮了。还在庆幸自己活过来了的丁太知道了事情真相之后,毫无留恋的去了。在丁太的孙子成成及孙女秀秀那里,阴谋的败露让他们有了人性及亲情的启蒙。但在她的二儿子丁如龙那里,这一切像是刚刚开始,更多的阴谋正在慢慢开启。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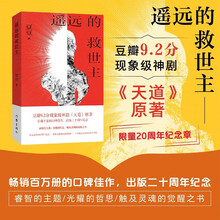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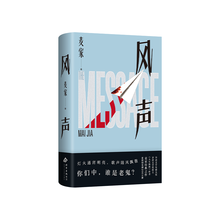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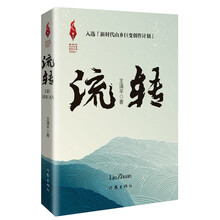
然而这不是讽刺小说。方方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闹市之中,在四官殿附近。方方讲得最出色的故事都发生在江汉平原的繁华之地。或许这块土地负荷太重,心酸的故事比幸福的故事要多。
老祖母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到头来反成了全家人的累赘。她喝“敌敌畏”自杀,不醒人事地躺在医院,更给全家带来无数的麻烦。她好赖活着时,一家人尚可用她及时备下的饭菜。可现在,被伺候惯了的一家子却反过来安顿她伺候她,还有巨额的医疗费都成了大难题。不等她断气,两个儿子已经在心里酝酿着如何把这沉重的包袱卸掉。大儿子丁如虎同意二儿子丁如龙的提议,将丁太送往她的乡下老家。
送老祖母上路的那一日是一个郊游的好天气,丁家的小辈是怀着风景这边独好的心情出发。一路谈笑风生,欢歌笑语。当他们发现汽车停在火葬场而不是老家黄陂时,只是略感蹊跷,他们之中没有人表示异议,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异议。没有人愧疚,因为大家都不愧疚。也许他们觉得这是老祖母最好的归途。
小说不是在作道德审判,作家展示的是亲情中的困境。这困境是由贫穷、狭隘和自私共同造成的,而贫困和狭隘又放大了人性中的自私,吞没了良知和亲情。小说中除了头脑精明的丁如龙,这个老祖母最喜欢的小儿子有着人性恶的特征:狡诈、虚伪、心狠手辣等,其余的人都是善良的。但是,就是这群善良的小辈将老祖母送进了停尸房。当物质的匮乏整个牵制了人的时候,善良居然显得如此软弱无力。方方告诉我们,良知和亲情是需要生长空间的!小说让读者自己在逼仄的居住空间和狭隘的心胸之间建立起联系。十二平米的小屋住着祖孙三代共五人,小屋又坐落在拥挤不堪的小巷之中。“一辆的士开进巷子,一巷人都手忙脚乱地移动把巷路挤得窄窄的床铺,叫骂声和灰尘一同高扬起。”小说中人们的怨忿就是打由这拥挤和混乱生发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观念冲突在这方寸之地显得分外尖锐,丁如虎连二婚的权利都被剥夺,就因为老祖母辛辛苦苦守寡几十年,自动获得对儿子的否决权。祖母哪怕能外出住一个月(比如住到丁如龙家),丁如虎就能把生米煮成熟饭。但是……连这样的机会都不可求(作家在这里干预了一下,使得机会成泡影,小说倒是充满了戏剧性,只是太狠了一些),难怪老祖母的离去竟然给小辈带来“解放啦”的感觉。
当然我们有理由追问,人世间的恶,是否都是由丁如龙这样的小人发端,是否必然在狭小的空间中爆发?我们相信精神背后的物质力量,也顺便给“物质变精神”找出一种解释。作为和弦,小说还写了医生王加英一家,瘫痪在床的母亲一躺就是十多年,给小辈的生活带来诸多的痛苦,久病无孝子!是时间加剧了这一亲情的困境?当王加英在成成的央求下给老祖母开死亡证明时,或许下意识中有着让街坊从老人病体的纠缠中解脱的念头。
方方的《落日》可以看成是《风景》的续篇,写的都是市井生活。笔触简洁,节奏明快,在该铺叙之处又不忘大肆渲染,很叫读者喜欢,不过《风景》中既有人世间的争夺和倾轧也有市井生活的温暖,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在《落日》中,则没有那一丝温情。利害的算计压倒了人伦,即时的快乐取代了亲情。连最年轻的秀秀在奶奶病危之际还是沉浸在一己的欢乐和快慰之中,毫无哀伤和愧疚之情,叫读者脊背发凉。风景是隐喻,落日也是隐喻。虽然两篇小说几乎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但是我们分明能感觉到十多年间作家的心态变化。她将人性中自私残忍的一面展示出来时毫无顾忌,她相信今天的读者心理能接受这样的叙述。或者作家就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写一部喜剧?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说过,“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更坏的人的。”起码读者在唏嘘感叹之余,觉得自己在良知和同情心这一层面高于小说人物,并能得到某种批判性的满足。(蒋原伦,from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