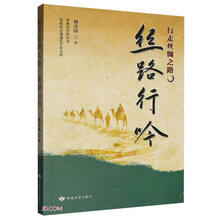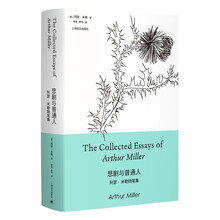父亲的人影刹那间消失了。她朝父亲人影显现的墙角看,墙角什么也没有。她希望父亲的灵魂在房里,在人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她希望能有一个无可战胜的鬼魂显魔力,她需要这个魔力的帮助,她要这个魔力帮助自己保住已经到手的粮食,她需要钱,她已经六年没有为自己添置新衣服了。除了在这张床上,没有人把她看作女人。她在韩家庄园看到韩夫人以后,感到自己依然是一个寒碜破落可怜的寡妇,身边的这个男人总是许诺帮助自己,可总是不兑现。在韩家庄园她感到韩先生回避的目光,自卑就在那一瞬的回避间膨胀起来。
……
书摘1
第六章
LUO HONG MI GUI LU
伊人站在窗口看河上的风景,她的手无力地扶在窗框上。窗框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那年老爷说秋后要重新把这楼油漆一遍。没有等到秋后老爷就归西了。那年老爷还说要接她到上海去住,眼看就可以去上海住……一个那么厉害的人怎么就被炸弹吓死了……那年老爷的身子已经不行了,一家之主倒掉了谁还有这样的闲心思做这些事。日本人来了,生意不好做。生意也还做着,钱没少赚,可这些钱没赚在自己的钱包里,都给人家弄走了。
河那边的田野,蒙蒙的绿夹着蒙蒙的黄。河上有船经过,船尾劈开八字样的水波纹。伊人听到水拍打河岸哗哗声响。想想也真可怕,自己住到这楼里快二十年了。女人的一生过去了一大半。年年倚靠在窗口看风景,窗口的风景年年一个样,可自己的心情早已不是从前。从前盼望老爷回来,一天又一天,不知道日光消融在水光中,还是水光消融在日光中。
现在还有什么盼望?儿子?儿子毕竟是儿子,他以后会有自己的女人。嘉树?除了儿子这些年来,她把命运不知不觉地系在了这位表兄身上。她为他担忧,她甚至怕他会像老爷一样,突然在哪一天离她而去。虽说他不怕日本人,但那边游击队的子弹是专打这些做日货生意的。
这几天她的右眼跳得厉害。左眼跳福,右眼跳祸。
“少奶奶。老太太叫你下楼说话。”
俏俏掀起帘子站在门边说。
“听到了。”她不耐烦。
俏俏穿着一件蓝底黑格子的小褂子,脸黄巴巴的。枯黄的刘海遮住淡淡的眉毛,一双细细的眼睛盯着她看。
伊人被俏俏看得心乱。她的任何什么事都瞒不过这丫头的眼睛。
李署长被日本人枪毙以后,母亲从上海逃到贝城来靠她过。母亲一个钱也不拿出来,所有的花销都从她这里开支。老爷在世时的一点积蓄怎么经得起这么花法。到最后只得把这楼卖掉。她已经想到最后一步了。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一切都被老爷在世的时候说中,老爷讲,有一天他不在人世了,她就要被冯家的人吃掉。
“你先下楼去。”伊人对俏俏说。
俏俏下楼去。伊人继续站在窗口看窗外的风景。真想变做一只鸟儿飞走。飞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可以让一个人清清静静地过日子,无忧无虑,她愿意到那个地方去。
俏俏又上楼来。
她对俏俏说:“我就下楼。”
阿翠移开嘴边的烟枪半睁着眼睛看着伊人慢慢地说:“嘉树要娶亲了。”她注视着女儿的脸。
伊人的身子在母亲喑哑的声音里微微一晃,一瞬间全身的血液冲到她的头上脸上。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声音是真的。嘉树上个礼拜还睡在她的床上。那夜他和她做了三次。临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他的手还伸到她的下身摸了一把。
伊人的身体像被人泼了凉水,不住地发抖,目光冰冷。母亲她也说过无数遍,不要把男人当做一景,无论这个男人眼下对你怎样,男人的好,不是听他的甜言蜜语,是看他肯拿出多少值钱的东西给你。是他离不开你的洞,还是你离不开他那根棒,要是你离不开男人那根棒,你的日子就到头了。
“你坐下来。”
伊人晃悠悠地在一张描着金线,绘着翠绿色荷叶粉色荷花的腰鼓形状的瓷凳上坐了下来。她呆呆地望着母亲,母亲横卧在烟榻上。眼前的情形好像梦中的幻影。但母亲的声音是真切的。
刚才那个喑哑的女声,是从烟榻上眼前这个灰色的女人身体里发出来的。
如梦如幻,一个礼拜前她还和嘉树睡在一张床上……这几年来她和嘉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过着不明不白的日子。他要她的身子,她也要他的身子。这个男人从她手上拿走了不少钱。他说过,以后要养她老。他说过,表兄表妹亲上亲。他背着她找了年轻的女人,要娶那女人了?那女人是谁?这事街上的人都知道了?反正他们迟早都知道了……
伊人呆呆地看着烟榻上的母亲。
她想从母亲的脸上看出,这些统统是街上无聊的人编派出来的假话,或者是一个梦。
这些年来她总是劝母亲不要吃大烟。母亲就是不听劝。还说,不吃这东西全身的病就要出来,譬如吃药。这些年她把自己同嘉树的关系也当作吃药。一个女人没有男人滋润,身上的病也要出来。早晚这个楼要被吃空。伊人心里空空的,想痛哭,却恍惚地冲着母亲微笑。微笑沉重地牵动她的嘴角,把她的脸扭曲得非常难看。
她看过嘉树的日本女人的照片,那照片上的日本女人是同嘉树有关系的,那女人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她问过嘉树,这个女孩是不是同他有关,嘉树不承认。
嘉树这么多年没有娶,她一直以为嘉树就这样和自己过下去了。至少他没有回日本之前就这么同自己过下去了。
“一个女人要拎得清。”母亲在淡黄的火苗的后面说话。
这是她听了三十几年的声音。拎得清怎样?拎不清怎样?一切都应验了老爷在世的话,冯家是一个无底洞。她和嘉树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无底洞,但自己的身子也是一个无底洞。除了嘉树能给她,没有别的男人能缓解她身体的焦躁。伊人痛苦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嘉树是你什么人?他是你的表兄。再过两年,他就四十岁了。成个家,留个种对得起冯家的祖宗。”
“你是什么人?你是穆老爷的太太。这个身份要时时记住。女人可以不守节,但寡一定要守住。”
两个细长的水滴一样的翡翠耳坠在一张枯黄的脸颊旁晃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