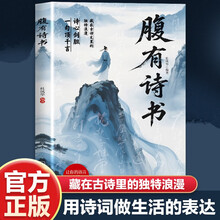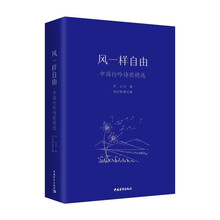李亚伟诗歌带来的愉快,不是指那种放弃“精神攀登”的轻松感,不是指那种廉价的生活幽默,更不是指那种在诗歌中用几个具有欢快效果的语词。而是指一个诗人在相对完好的天性中的诗性言说。语言之于李亚伟,不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天赋的才能,是他健康天性的存在方式。
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如果非要给当代汉语诗一项“源头性”的桂冠,李亚伟当是一时之选……几千年形成的汉语传统被他撕裂、蹂躏,又用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这种才华与生俱来,毋须觉醒。
——张小波
李亚伟诗歌带来的愉快,不是指那种放弃“精神攀登”的轻松感,不是指那种廉价的生活幽默,更不是指那种在诗歌中用几个具有欢快效果的语词。而是指一个诗人在相对完好的天性中的诗性言说。语言之于李亚伟,不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天赋的才能,是他健康天性的存在方式。
——李震
就像金斯堡之于“跨掉的一代”一样,真正能体现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流浪、冒险、叛逆精神与实践的,无疑是“莽汉”诗派,尤其是李亚伟本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亚伟都可以称为源头性的诗人,直接启迪了“后口语”的伊沙和“下半身”的沈浩波等人。
——李少君
在当代诗人里,李亚伟也许是最注重历史与地理的诗人。纵深的历史感觉使他能够轻视当代同行,轻视单一观点,他愿意从不同的角度叙事,不透露文学抱负,仅仅简单地重复刻划走投无路的感觉就能加强诗歌的复杂性,他用巧妙的评论在诗句中轻轻一笔带过就嘲讽了当代同行的功利之心。
——张万新
从李亚伟的诗中,我感受到所谓的“男人”特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野,二是粗。野体现在我行我素,天马行空,粗体现在想爱就爱,随心所欲。我以为“男人”在这里不是一种性别的记号,而是一种权力的记号,因为每个男人骨子里都有做“王”的企图。而王者的天下是打拼出来的,打拼总是从肇事开始。
——李德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