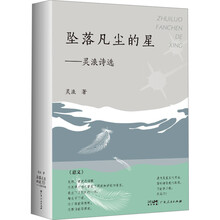起意编一本20世纪中国新诗选,其中一个原因,是觉得已有的一些选本为了追求全面,入选的诗人过多,有诗名的选多选少总得选吧,这样下来的一个结果,好像是点人头,追求全面差不多变成了全面照顾,漏了谁都不太好。从好的方面讲,此类的选本比较尊重文学史的实际情形,尊重尽可能多的诗人的劳动和成绩,毕竟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是有那么多的人在写诗,选本岂可轻易编排进某些人的作品,而排斥另外一些人及其作品?
但这样一来,一般的读者拿起一本诗选,就觉得不大容易找到头绪了,这么多的诗人,每人入选作品的数量没有多少差别,字面上混成一片,弄不好读着读着脑子里也混成了一片。从这样的读者立场出发,无论如何选本还是得狠点心去“选”,能够选到让读者眼亮心明的程度最好。
跟前的这本《中国新诗: 19162000》,也做不到让人心明眼亮的程度,却是把这当成一个目标的。书中共选编了六十几位诗人的二百余首作品,这样一个自控的规模,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岂止如此,选本甚至遗漏了一些曾经产生过不少影响的诗人及其作品。由此可以对这个选本进行挑剔。但是我也听到了来自相反方向的挑剔:有几位朋友看了目录之后说,还不够狠心,还可以再减少几个人,再减少一些作品,再精些。可商讨的地方当然不仅仅就这一个方面,譬如,单就入选者的作品数量来说,互相之间显然也不那么“平衡”,谁谁谁是不是选得太多了,谁谁谁选得太少了?从作品本身来考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首替换下这一首更好些?
其实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这表明,每一个提出问题的人都有一本自己心目中的诗选,它们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和分歧,甚至是根本的对立。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对眼前的这本诗选进行增删改动,乃至另起炉灶,以完成个人心目中的诗选。我倾向于用这种态度和方式来解决差异、分歧和对立,而不是大家非要达成“共识”不可。各个单独的存在之间,可以通过“对话”来沟通,但不可有以此代彼的霸道,同时也决不可屈从于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为眼前的这本诗选辩护的一个理由。
所选的诗作,无疑应该还原到它们所从中产生的时代和文学史背景里去理解;以近一个世纪为时间跨度的选本,无疑也应该通过作品反映基本的文学史情形。在这一取向上,这个选本显然也有它的追求。但是,这个追求的愿望不可太强
烈,文学史的要求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在要求今天的读者尊重文学史因素的同时,也必须尊重读者今天的欣赏趣味和判断标准。也就是说,不能仅仅要求读者走进文学史,我以为,比这更重要的,是让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走进今天的读者中。如果一定要追问这本诗选的编选宗旨的话,这当是很重要的一点。毕竟这是一部作品选,而不是文学史的作品编年一类的东西,而且,这部诗选预想的是尽可能广泛的读者,而不是要为文学史负责的专家和某些圈子内的读者。
那么,什么是判断作品本身优秀与否的标准呢?什么是今天的读者的欣赏趣味呢?显然,不可能存在一个斩钉截铁的标准和整齐划一的趣味。这个选本有意识地瓦解一段时期内所谓的诗史“主流”的观念和此一观念统摄下的作品“定位”、“排序”,同时也有意识地不以另一种单一的观念和趣味取而代之,虽然带有编选者个人的主观倾向,还是想尽可能地呈现出多元的诗观和诗作面貌。
也正是从呈现多元诗观的意图出发,选诗的同时还选录了一些相关的文字,或为他人的评论与描述,或为诗人的自我揭示与剖露。统合起来,这些文字未尝不可以看成一部扼要的诗论选。这些与诗相关联的文字,像诗作之间存在沟通、差异一样,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彼此呼应和种种不一致,集合在一起,确有“众声喧哗”的效果。希望此种简明的选录方式,不仅能够为读者提供阅读理解的参照,而且能够开拓阅读和理解的空间。这许多种声音,自然会有助于克服某一种或几种单调的声音对阅读和理解的可能性的有意无意的限制。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选本的编排顺序:同一作者的诗作,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在一起;作者的先后,对应予入选的最早一首作品的写作时间的先后。大致上,这与文学史的发生序列相符。编者曾经想标明每一首作品的写作时间,后来发现很难做到,但还是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努力。请有心的人注意作品篇末那些写作(而不是发表)的时间。
在持续时间不能算短的选编过程中,我也持续地接受着来自师友的鼓励和实际帮助,对于我,这其实早已成为日常经验中重要的部分,这一项具体的工作,又把这一重要的部分具体化了。我同时以为,如果把这仅仅看成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我就太狭隘太自以为是了,至少它是对一件事情的支持,这一件事情的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中国新诗为中心联结、汇聚起许许多多的个人,这本诗选也正是献给许许多多的个人的。
“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