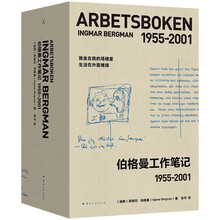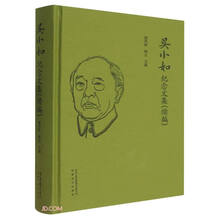一缶蜜茶,半支素烛,主人的深情。
“今夜竟挂了单呢,”年青人想想暗自好笑。
他的周身装束告诉曾经长途行脚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走到这样冷僻的地方,即使身上没有带着干粮,也会自己设法寻找一点东西来慰劳一天的跋涉,山上多的是松鸡野兔子。所以只说一声:“对不起,庙中没有热水,施主不能洗脚了。”
接过土缶放下烛台,深深一稽首竟自翩然去了,这一稽首里有多少无言的祝福,他知道行路的人睡眠是多么香甜,这香甜谁也没有理由分沾一点去。然而出家人的长袖如黄昏蝙蝠的翅子,扑落一点神秘的迷惘,淡淡的却是永久的如陈年的清香的烟。
“竟连谢谢也不容说一声,知道我明早什么时候便会上路了呢?——这烛该是信男善女们供奉的,蜜呢?大概庙后有不少蜂巢吧,那一定有不少野生的花朵啊,花许是桅子花,金银花……”他伸手一弹烛焰,其实烛花并没有长。“这和尚是住持?是知客?都不是!因为我进庙后就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连狗也不养一条,然而和尚决不像一个人住着,佛座前放着两卷经,木鱼旁还有一个磬,……他许有个徒弟,到远远的地方去乞食了吧……”
“这样一个地方,除了俩和尚是什么都不适合的……”
何处有丁丁的声音,像一串散落的珠子,掉入静清的水里,一圈一圈漾开来,他知道这绝不是磬。他如同醒在一个淡淡的梦外。
集起涣散的眼光,回顾室内:沙地,白垩墙,矮桌旁一具草榻,草榻上一个小小的行囊,行囊虽然是小的,里面有破旧的物什,但是够他用了,他从未为里面缺少些什么东西而给自己加上一点不幸。霍的抽出腰间的宝剑,烛影下寒光逼人,墙上的影子大有起舞之意。在先,有一种力量督促他,是他自己想使宝剑驯服,现在是这宝剑不甘一刻被冷落,他归降于他的剑了,宝剑有一种夺人的魅力,她逼出青年人应有的爱情。他记起离家的前夕,母亲替他裹了行囊,抽出这剑跟他说了许多话,那些话是他已经背得烂熟了的,他一日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也决不会忘记那些话。最后还让他再念一遍父亲临死的遗嘱:“这剑必须饮我的仇人的血!”
当他还在母亲的肚里的时候,父亲死了,滴尽了最后一滴血,只吐出这一句话。他未叫过一声父亲,可是他深深地记着父亲,如果父亲看着他长大,也许嵌在他心上的影子不会怎么深。他走过多少地方,一些在他幼年的幻想之外的地方,从未对连天的烟波发过愁,对蓊郁的群山出过一声叹息,即使在荒凉的沙漠里也绝不对熠熠的星辰问过路。起先,燕子和雁子会告诉他一声春秋的消息,但是节令的更递对于一个永远以天涯为家的人是不必有所在乎的,他渐渐忘了自己的年岁,虽然还依旧记得哪一天是生日。“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他曾经跟母亲承诺过。曾经跟年老的舵工学得风雨睛晦的知识,向江湖的术士处得来霜雪瘴疠的经验,更从背箱的郎中的口里掏出许多神奇的秘方,但是这些似乎对他都没有用了,除了将它们再传授给别人。一切全是熟悉的了,倒是有时故乡的事物会勾起他一点无可奈何的思念,苦竹的篱笆,络着许多藤萝的;晨汲的井,封在滑足的青苔里的,……他有时有意使这些淡漫的记忆浓起来,但是这些纵然如秋来潮汐,仍旧要像潮汐一样的退下去,在他这样的名分下,不容有一点乡愁,而且年青的人多半不很承认自己为故土所累系,即使是对自己。什么东西带在身上都会加上一点重量,(那重量很不轻啊。)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想送他一个盛水的土瓶,但是他说:“谢谢你,好心肠的姑娘,愿山岚保佑你颊上的桃红,我不要,而且到要的时候自会有的。”
所以他一身无赘物,除了一个行囊,行囊也是不必要的,但没有行囊总不像个旅客啊。
当然,“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他深深地记着。但是太深了,像已经溶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竟似与自己无缘。
今晚头上有瓦(也许是茅草吧),有草榻,还有蜡烛与蜜茶,这些都是在他希冀之外的,但是他除了感激之外只有一点很少的喜悦,因为他能在风露里照样做梦。
丁丁的声音紧追着夜风。他跨出禅门(这门是圆的)。殿上一柱红火,在幡帐里跳着皈依的心,他从这一点静穆的发散着香气的光亮中走出,山门未闭,朦胧里看的很清楚。山门外有一片平地,正是一个舞剑的场所。夜已深,星很少。但是有夜的光。夜的本身的光,也能够照出他的剑花朵朵,他收住最后一着,很踌躇满志,一点轻狂圈住他的周身,最后他把剑平地一挥,一些干草飞起来,落在他的袖上。带着满足与珍惜,在丁丁的声息中,他小心地把剑插入鞘里。
“施主舞得好剑!”
“见笑”他有一点失常的高兴,羞涩,这和尚什么时候来的?“师父还未睡,清韵不浅。”
“这时候,还有人带着剑。施主想于剑上别有因缘?不是想寻访着什么吗?走了这么多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