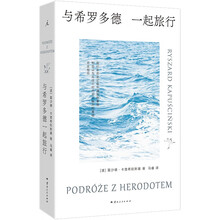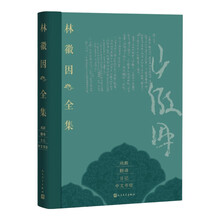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往往有几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复旦大学来说,有四个时期影响深远:1905年脱离震旦大学另立复旦公学,使复旦的根系挣脱了教会大学体系的束缚,迈开了自主的脚步。倘若没有这一艰难的从头起步,随着1952年中国教会大学的彻底消失,震旦烟消云散,复旦更无从说起。第二个时期是抗战西迁重庆,复旦在1942年由私立改为国立。表面上看,复旦从此离开了“民间”传统,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教育规范之中。然而在这一转变中复旦获得了经济上的有力支撑,使学校能够在大后方坚持下去,为民族培养急需的抗战人才。据《中华民国档案汇编》中的资料记载,仅仅1939年复旦大学的财产损失就高达五十四万余元,而同期的南开大学更是高达三百万元。对于财政拮据的私立大学来说,这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所著名私立学校分别在1942年、1946年改为国立大学。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复旦难忘的第三个时期,复旦汇聚了华东地区十余所高校的文理科精英,一跃而起,成为中国最高层次的大学之一。而此时,全国的私立大学一律改为公立,绝大部分拆解到其他高校。如果复旦仍为私立,恐怕此时也不免销声匿迹。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复旦迎来了发展期最长的第四个时段,这一时期里里外外的推进力接踵而至:1984年后进入少数几所国家基本建设大学的行列,世纪之交又迎来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时期。在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一波又一波大潮中,复旦总是得天下之先,临近百年之时,焕发出无限青春。
复旦的文学传统与创作起伏,与上述四个时期有密切关系。1905年筹备成立复旦的六个“干事”中,于右任、邵力子后来都是文学成绩斐然的名家。而后入复旦学习或任教的文学名流络绎不绝:任复旦公学校长的严复、进入复旦公学学习的陈寅恪、组织复旦剧社的洪深、讲授文学的叶圣陶、翻译教学两不误的傅东华、诗人意气的刘大白复旦的这种文学气象,得益于上海当时的特殊文化地位。五四之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出版业聚集于上海,引来了大批的文化人。复旦地处于此,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复旦文学家大多继承了“学者与作家”兼而有之的五四文化人特色,很多人从事文学创作,也进行学术研究。谢六逸、郑振铎、方令孺等人皆如此。这种风格也影响着稍后的一批人,使复旦作家都有些书生气。1926年进入复旦、1949年后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既擅长写小说,又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方面,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而在抗战时期西迁重庆之后,大批文化青年来到复旦。他们身处民族危亡的生死线上,行动大于思维,文学与学术语境大幅分离,呈现出更多的实践性与理想冲力。这一时期进入复旦学习的冀 、绿原、邹荻帆,任教复旦的胡风、端木蕻良、储安平、曹禺等人,都有更多的专业作家气质。复旦在重庆的年份不算长,但这一时期培养的作家数量颇大,不少人以后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复旦文学的这一特殊阶段的丰硕收获,来源于抗战时期重庆的特殊地位。作为战时首都,大批文化人云集山城,为抗战宣传,为文化之火,为学术相传,也为文化人的生计,流离的青年与漂泊的文人都在复旦找到了一展身手的天地。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地缘”环境是:中国当时的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等,都没有搬到重庆,复旦在重庆的“聚集效应”自然放大。这也是历史提供的一个特殊文化空间。而在1952年后的复旦,已经是国家教育战略中的排头兵,万千学子心向往之,各地英才源源不断而来,其中的文学萌芽不可计数,理应作家辈出。然而事实并不尽然,1966年前复旦培养的作家在中国作家协会与各省作家协会的名录中数量可观,但其中大部分是评论与研究者,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方面的大家并不多见。这种情况不仅出现于复旦,全国大学几乎都是这般状况。其中的重要原因,是1952年之后,高校的文学系科将主要的方向确定在培养研究与教学人员上,并不鼓励甚至压抑大学里的文学创作。在一切都被“计划”的年代,这种培养模式似乎理所当然,但与国际文学教育经验大不相符。美国及欧洲很多大学都有“Creative Writing”硕士学位,专力培养创作意义上的作家,成效斐然。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秩序大乱。大乱中复旦中文系破天荒地开设了“文学创作”专业,乱世中培养了梁晓声等小说家,也算一幸。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复旦陡然增加了一大批文学良将。仅中文系就收进了卢新华、张胜友、胡平、王兆军、李辉、张锐、李晓等十余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创作人才。而经济系当时意想不到地成为复旦诗歌的高地,许德民等人创办的“复旦诗社”在中国校园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之后,复旦学生几乎代代出作家,而且作家的创作风格和价值观念千差万别。这离不开复旦温润而多样的文学气候,几乎每一种文学种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开花的土壤。马骅、韩博、卫慧、素素这些作家能出自一个校门,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自由的象征。
另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更值得深思:很多复旦学人在学术生涯的丰收之年,却开始了散文创作的青春期。贾植芳、潘旭澜、吴中杰、葛剑雄、周振鹤、许道明、骆玉明都在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获得文学界的热烈反响,形成了复旦的校园“创作圈”。更加令人注目的是,复旦越来越自觉地将创作视为自身发展的支撑点之一。1989年第一次开办了“作家班”,培养了虹影、凡一平等来自生活深处的青年新锐。近几年又引进了王安忆等著名作家,并开始招收以创作为主要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一个复旦文学的新时期,隐约可见。
回顾复旦的历史路径,文学是其中延绵不绝的篝火。为纪念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也为了这难忘的文学历程,这里编辑了《巍巍学府文章焕 ——复旦作家作品选》和《日月光华同灿烂——复旦作家的足迹》两本文选。“复旦作家”既包括毕业于复旦的学子,也包含曾任教于复旦的教师。收入的文字,基本上按照复旦文学后浪推前浪的历史流脉排列先后。这两本集子所能包容的,仅仅是复旦文学的一部分。当我们再次抚摸这些复旦人的文字,再次回想这些复旦人风雨兼程的奋斗,不禁感慨满怀。其中的一些作家是我的师长,曾经给以我难忘的教诲。记得是在1981年,中文系举办书法展,学生会派我去请朱东润先生写一幅参展作品。一进朱先生家门,只见他手提大茶壶,从楼梯上腾腾走下来,丝毫不像已经八十五岁的老人。我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问我什么时候来取。我说书法展明天开幕,今天就想带回去。朱先生顿时脸色一沉,严肃地说:“看来你中国文化学得不好,不懂得礼仪。
你这叫‘请字’,是件庄重的事情,起码要提前一个星期来说。一幅字写起来很快,我马上可以给你,但这不符合中国文化的道理。这样吧,看你来得挺急,三天以后来取。”听罢这番话,心里又惭愧又感激,连声向朱先生道谢。我的硕士论文导师潘旭澜先生、博士论文导师贾植芳先生都在晚年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发表了《太平杂说》、《狱里狱外》等有广泛影响的文化散文,作为学生一辈,深为
他们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所鼓舞。这样的教育,只有来到复旦,在先生们身边才能获得。也正因为有这样复旦作家的不息奋斗,我们才能说:复旦,无愧于中国百年文学!
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复旦下一个百年之时,会如何回顾自己的文学履痕?可以说,复旦今天所获得的发展能源,是历史以来最强的。社会与民族都对复旦有着巨大的关注,复旦秣马厉兵,正在进入历史的最佳位置。复旦如何为民族的人文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文学创造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期待着,我们责无旁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