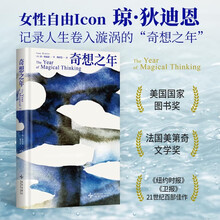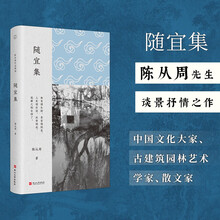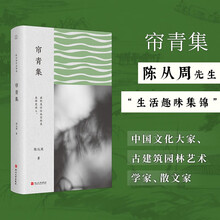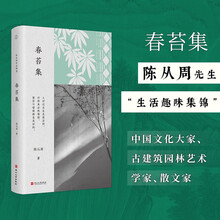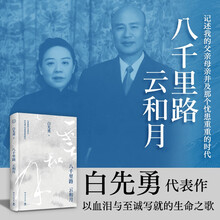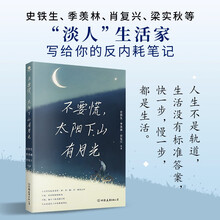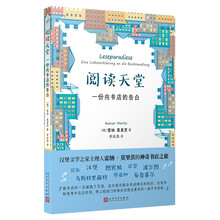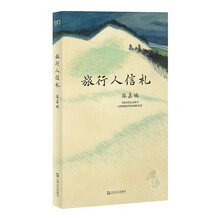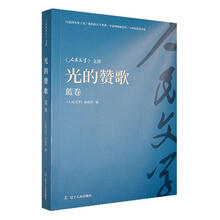“边缘批评文丛”主要收集中国学人在海外的文学批评文字与文化研究成果。“文丛”作者大都原是国内知名评论家,近二十年来到海外游学。由于身份、对象和语言的缘故,他们在海外学院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基本属于“边缘学科”。 然而,当他们在海外获得学位取得教职或频繁越界施行以后,他们的批评文字在国内学术界又成为一种“边缘的声音”。“边缘”其实可以或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中心话语。艾德华·萨依德也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但对于“边缘批评文丛”的作者们来说,“边缘”与其说是自觉追求,不如说是某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学术处境。“边缘”所标示的,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空间位置,而是批评者在中心与中心的夹缝间的游走穿梭。“边缘”作者挪用种种灰历混杂的理论策略,调整组织自己的文本经验,应对扑面而来的历史情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