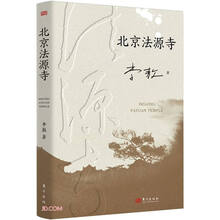对于任一具体作品,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美学的历史的价值,因此,文本解读的精确度和深刻度决定文艺批评的质量。文本解读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或从创作主体的风格特征、人生关注、感情态度、创作方法的剖析入手;或从创作对象即形象中所蕴涵的生活的诸多方面,现实的和历史的各层面的阐发着眼。取径虽然多方,约而言之却不外两途:一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法,即从作家所诉求的种种情状追溯他所钟情的人生问题及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一是伯乐《相马经》所说的“按图索骥”法,即从作品所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论证作家如何将生活转化为艺术。这两种路数自然会有交叉,有重叠,但其批评建构和基本倾向却是显然有所区别的。本书作者顾鸣塘所择取的为后一种路数。<br> 这种方法必须对产生作品的社会状况了然于胸,论证中要掌握大量材料乃至精确的统计指数,才得以阐明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生态,进而观照鉴别对象的形象合理性、真实性和合于美学比例的程度。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排除游谈无根和向壁逞臆;但稍一不慎也易走入误区,因耽爱资料而失于节制,陷入烦琐考据和议论枝蔓;或醉心于从资料去发微索隐,于是便从别一岔道与游谈臆测会合。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人们对这种畸形现象见得太多了。<br> 令人欣喜的是,本书作者避免了烦琐和枝蔓,也不分心于比附与索隐。本书所论证和据以论证的材料,是环绕在《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周围的原生态,全书紧扣着小说的形象,论列了各色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疏通了小说形象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关联和呼应。既以人生实况印证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之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由,也时刻在显示制度性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状貌时,以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言谈作出反证,使艺术与人生互相映衬而彼此都得以彰显。由于本书所提供的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的完备和翔实,纲目毕具,遂使本书不仅大有裨于解读《儒林外史》,而且也使本书自身成了清代早中期社会性质的百科式的论著。<br> 本书论证的重点也和吴敬梓小说所主诉的内容同向。书中第三章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程式、运作,以及竞逐于这一制度下的士子心态的论叙,是全书篇幅最多、情况最周备的部分;单就这一章言,割取出来便可成一本介绍科举制度的专书。吴敬梓嫉视科举和时文,甚于别的各种社会弊害,显然是因为作为社会文化承担者的儒林群体,统统受这个制度的牢笼和荼毒,人格被扭曲,因而导致了文化的偏枯和颓败。吴敬梓将此视为一切文化弊病乃至社会弊害的总根而给以辛辣的讽刺。正是儒林中人的颓败以及远不止是儒林的颓败,使吴敬梓敏锐地察觉出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儒林外史》的深层内容,便是从这大群可笑可悲的人物活动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文化危机。<br> 吴敬梓是封建末世察觉了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位智者,其历史作用如用世界范围的杰出人物来比拟,则正像欧洲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提早发出了呼召文艺复兴的先声。吴敬梓比后起的龚自珍提早了一百年发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那样的沉重叹息。<br> 然而,在吴敬梓忧心忡忡地公心讽世时,中国大地上的秀才们、官员们、绅士们、清客们、斗方名士们,优倡皂隶以及上上下下各阶层、各行业的芸芸众生,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却在扰扰攘攘、孜孜矻矻、晕头转向、煞有介事地奔走着他们的功名、权位、浮名和各色各样的利益。社会在沉沦,在陵夷,却仍如常地运转着,和往昔毫无异样。本书所提供的,便是这个社会图景,它的风貌、风习,包括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诸种色相。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