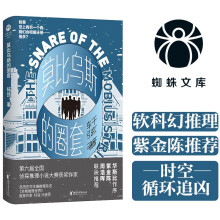十几年来,我们的文坛总是喷泉式突进,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观常常不择而出,超出人们的理性边界。余秋雨热是这样,易中天热同样如此。看看易中天的学者生涯,以前写过数量不算少的文艺学、文化研究论著,字字殚精竭虑,却像雨水落进沙漠里,没有多大的社会反响。而自从上了中央电视台讲三国,顿时欢声一片,随后就是出版社和如云的“粉丝”,热闹非凡。因此说:现象大于个人,易中天还是那个易中天,围绕他的人群和声音却寒热两重天,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文化中产阶级”的文化欲望
一种文化产品在社会上热起来,总是有它的精神需求。需求越大,热度越高,这正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群热了易中天?初初看去,似乎是热爱历史的广大读者,细细根究,却并不尽然。这其中有一份文化情缘,更有一种文化青涩。中国文化的一个大优势,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极其罕见的静态文化资源。中国历史辉煌于唐代以前,那时候的欧洲文化过于萧瑟,压抑在基督教神性的神秘气韵中,人的活性还远远没有呈现。而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脱离人间伦理,演绎出种种富于人类悲欢的精彩故事。就文学而言,自公元360年后,欧洲文化被《圣经》叙事大一统,进展甚少。而中国文学已经由简人繁,经典迭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自豪,也是中国人潜意识中的骄傲。不过这种自豪与骄傲在贫穷的时代隐而不显,因为大家还汲汲于饮食男女,无暇体会自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归属。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几何级数递增,年轻的一代普遍受过良好的基本教育,同时又感受到来自全球化的文化信息。稳定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生活情景:很多人在经济上还处于小康阶段,但在文化上已经达到中产水平。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他们拥有的信息、潜移默化的生存理念、对人生的向往已经高出了自身的经济地位。这时候,《故事会》之类的通俗读物远远不能适应他们的品味,而精致的纯文学之类读物又超出了他们的文化智趣。于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文化产品势必走红:它投合着人们对历史辉煌的自豪,又不那么讲究穷根问底(否则太累)。它不大具备“学习”功能,因为文化中产阶层需要的是放松,是轻度的有闲;同时它又充满文化的气氛,似乎在体会着某种深刻的东西。什么产品最符合这样的文化“定制”?“谈古”几乎是不二法门。讲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深沉,至少是貌似深沉。历史本身又布满了疑云,正好用来编织故事篓子,娱乐性与文学性齐备。这样的文化产品正是文化中产们的最佳文化伴侣,最能激发他们的言说欲望。考虑到这一点,“易中天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易中天,还会有其他的文化人来填补缺位,这是时代的定数。
这样说绝不是贬低易中天的文化等级。我看易中天在电视台上讲三国,言辞很用心,有时还很小心,在适应大众化听感的时候又尽量保持儒雅的严谨。随后阅读他的《品三国》文字,深深感受到他梳理史料、掂量人物的一番苦功。我想,易中天初登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时,大概是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庄严意识,欲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然而现今是个受众的时代,文化中产们硬是把易中天来个变形记,剔去他的学理气质,放大他的通俗一面,活生生地将一个书生变造成讲故事的文化小生。文学人经常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万个人里只有一个易中天,就是那个说书的教授。我们能责怪文化中产的浅薄吗?显然不能!而且非但不能,还应该击节欢呼。这是文化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其中包含着感性与理性的相互激荡,是人们在幼稚与成熟之间的攀爬。当人们度过这文化消费的青涩期,当易中天终于不再热,大家终将发现自己的种种误读,那时,社会文化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文化精英”的价值焦虑
易中天的《品三国》,严格地说是“越界飞行”。他的本分是文学研究,忽然跑到历史的园子里说东道西,而且还是历史阵列中最复杂难辨的“三国”一段。说他“大胆”决不过分,可说他“妄为”却要斟酌。
从文学到历史有天壤之别,身为大学教授的易中天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文学理论家的历史功底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历史学家,难道易中天不怕自己的种种学术漏洞被人揪住死打,坏了学人的声名吗?当然不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类被人冷嘲热讽地“逗”了一番,至今余波不断,易中天看在眼里,岂会掉以轻心。然而如此险境,易中天还是“偏向虎山行”,这其中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苦心或大志。学术上忌讳“伐心”之说,我不敢探讨易中天的用意,但有一种感觉还是想坦然言出,因为这涉及当代中年知识分子普遍的状态: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学人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不可消解的价值焦虑,很难在纯粹的理性中获得自信和快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在苦难中承担着社会良知的重任,与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细分不足,公众化倾向却热情高涨。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分工的粗细和深化是历史的趋热,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按道理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静心于学术的历史条件,政治的干扰少了,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也相对改善,知识分子可以恪守本分,尽享“乐道”的喜悦。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中年知识分子陷入了价值危机:以往的知识体系带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烙印,失去了言说价值,而新的话语体系又来不及消化和再造,处于欲言不能的尴尬。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勉力言说,又看不到坚实的历史价值,有些空说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来自社会环境,也来自学者自身的局限。从社会方面来说,中国传统上是个“有国家无社会,有群体无个人”的共同体。国家政权垄断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社会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间组织,国家十分庞大,但民众却一盘散沙。相对应的是,民间生活中个人没有充分的自由空间,人生道路被规定在传统与习俗的划定范围中,鲜有活泼的个性。100多年来,这一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其中的遗传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力量。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的那种思维向度和批判体系,往往不能获得社会的回应,启蒙的困顿和寂寞的清冷屡屡可见。通俗点说,知识分子辛劳一辈子,也许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生命的价值何在?当然,如果能够像康德那样,固守寂静的思想小屋,在纯粹理性中自得其乐,那也是可贵的境界。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来自伦理世界,骨子里崇尚实践理性。假如不能在现实可见的世界里获得肯定,必然寝食难安。这种文人品性逼着自己一定要介入当下的历史,否则就白活了。
易中天之所以“品三国”,其实也是在寻求介入社会的通道,大有传统士人的道德冲动。他从文学研究而文化研究,由文化研究而历史研究,努力中有一种寻找,表现了强劲的行动力。很多知识分子一面发着牢骚,一面无奈地做着自己也觉得大有疑问的“事业”,比起易中天,少了些探索的激情。但是,易中天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带着尴尬相:他做不到“想说就说”,更不可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要变个声调,把学术的“美声”转成“通俗”,这就犯了大忌,怎么看也不像个教授,倒像个讲故事的。况且,语调是有惯性的,易中天喜欢将古代的职官、语词翻译为现代白话,甚至是时尚的流行语,仔细考量,有点大而化之的油滑。这当然是转型中的问题,也许冷静下来就会自我调整,但这还是暴露出一种困境: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左右为难的时代,无论哪种生存都有不可摆脱的缺憾。易中天的越界飞行也许是一种挣扎,热闹遮蔽不住隐约的空幻,《品三国》上百万册的发行量证明的是纯学术的悲哀。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