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谁有一支彩色铅笔长得可以在天顶上作画,躺在床上可就是一种十全十美别无他求的经历了。但是,这一套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室内用的家用设备的一部分。我自己琢磨,这事可以由几桶Aspinall和一把扫帚对付起来。只是如果你真的像模像样挥舞起扫帚,饱蘸颜料涂抹起来,那你的脸上又一准会滴满淅淅沥沥五颜六色的颜色,仿佛什么奇怪的童话雨下起来;这却就是其诸多不利因素了。我看在这种艺术创作形式里,只有坚持黑与白二色为宜。从这点出发,白色的天顶确实是大有可为之地;事实土,一块白色天顶派上用场,我以为这也是它惟一的用处。
倘不是这种躺在床上的美丽的试验,我没准永远也发现不了它呢。多年来,我一直在现代房子里寻找一些空白的空间往上画画儿。纸是太小了,画不下什么真正让人联想丰富的图案;如同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说的:“我需要巨人。”但是当我试图在我们大家居住的这样的现代房间里寻找这些干干净净的空间时,我失望了一次又一次。我见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图案和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像我和我的欲望之间悬挂起一道精致的链圈眼幕。我检查墙壁,令我大感惊奇,我发现墙上早贴上了壁纸,而且还看到壁纸上早布满了许多非常没有意思的图像,全都看上去彼此相像,有些不伦不类。我尤其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随意涂抹的符号(一个符显然不会赋予什么宗教的或者哲学的意义)竟这样洒满了我这些漂亮墙壁,像一种天花。《圣经》里说:“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我认为,它一定是在指壁纸。我看到土耳其地毯上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颜色,简直与奥斯曼帝国一样,要么也像称之为“土耳其软糖”的果脯。我其实不清楚“土耳其软糖”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不过我以为它是“马其顿大屠杀”呢。我走到哪里都感到心灰意冷,手持铅笔或者画笔刷,眼见别人早已抢先我一步,把墙壁,把窗帘,弄得花里胡哨,连家具上都是他们那些孩子似的野蛮的图案。
我委实记不清星期六(四天前)我对多罗西·B夫人的评价。确切地说那天发生的是这么回事:大家正好在谈论她,我也直率地说我觉得她缺少魅力,也不风趣。我想她的年龄在二十二三岁之间吧。除此之外,有关她的情况我所知甚少。当我想起她时,没有任何栩栩如生的回忆出现在我的凝思中,映入我眼帘的惟有她姓名的字母。
星期六我睡得相当早。然而到了两点左右,风刮得紧了,我不得不起床把一扇没闩住的百叶窗关好,是它把我吵醒的。我稍稍回顾刚才睡着的那一小段时间;驱走了疲劳,没有不适,没有梦,我很欣喜。我刚刚重新躺下,便又马上入睡。过了一段难以估摸的时间,我渐渐地醒来,确切地说是渐渐醒在一个梦的世界里。起初,我无以区分这个梦幻世界与平时睡醒后才感觉到的真实世界,这个梦幻世界是那么的清晰。我躺在特鲁维尔的海滩上休息,这海滩同时又成了一个陌生的花园里的吊床,一个女人脉脉含情地看着我。她便是多罗西·B夫人。比起早晨我醒来认出了自己的卧房时,我并未感到更为惊讶。不过,那时我对梦中的同伴那神奇的魅力已没有更多的感受,她的出现曾激起过我的对其肉体和心灵的强烈渴慕也减弱了。当时,我俩神情狡黠地对视着,正在创造一个幸福和荣誉的奇迹,对此,我们心照不宣,她是这个奇迹的同谋,我对她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可她却对我说:
“真傻,谢我干什么,难道你没为我做同样的事吗?”
这一感觉(实实在在的),即我也为她做了同样的事,使我如痴如醉,仿佛这象征着最亲密的结合。她用手指做了个神秘的示意,并微笑着。我好像已经和她融为一体,明白她的意思:“你所有的敌人、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遗憾、所有的怯懦不是烟消云散了吗?”我尚未开口,她却听见我在回答:她轻而易举地成了胜利者,摧毁了一切,痛痛快快地吸引住了我痛苦的身心。她挨近我,双手抚摩着我的脖子,慢慢地撩起我的髭须,然后对我说:“现在我们去和其他人接触,让我们走进生活吧。”我心花怒放,精神抖擞地去履行这幸福的约会。她要送我一朵花,于是便从酥胸中央取出一朵黄里透红、羞闭着的玫瑰,将它插在我的衣服扣眼里。刹那间,我为一种新滋长的快感所陶醉。这朵插在我衣服扣眼里的玫瑰开始发出爱的芬芳,那香气直扑我的鼻孔。我发现我这种不为己知的兴奋扰乱了多罗西的神思。正当她的眼皮(我为神奇的意识所支配,竟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东西。我肯定)微微痉挛,泪水将夺眶而出之际,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眼泪。这是她的眼泪,我可以这么说。她靠近了我,仰起的头挨着我的脸颊,我能凝视着她的脸庞,尽情享受那神奇的恩泽和迷人的活力。她从鲜润含笑的嘴中伸出舌头舔去我眼角的泪水。继而,随着她嘴唇发出的轻咂声,她将眼泪咽了下去,我感到仿佛有一个陌生但更亲热、更撩人的吻直接印在我的脸上,我猛然醒来,认出了自己的卧房,就像临近地区暴风雨中紧跟在闪电之后的一声雷鸣,与其说是令人眩晕的幸福回忆接踵而至,不如说它已和确实得让人震惊的虚幻和荒谬化为一体。不管我怎样苦苦思索,多罗西·B夫人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前一天的那个女人了。我和她的几次接触所留在我记忆中的淡淡的痕迹几乎被抹去,就像汹涌的海潮退却后留下的陌生痕迹。我急不可耐地想再看到她,我出于本能想给她写信,但又犹豫不决。聊天时若提到她的名字,便会使我战栗,使我想起那天晚上之前她那并不
出众的容貌——和上流社会任何一个平庸的女人一样,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却比那些最高贵的太太或最使我兴奋的际遇具有更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不该主动去看她,而若为另一个“她”,我会奉献出一切。每一个时辰都在一点一点冲淡在我的叙述里已经走样的这个梦的回忆。它越来越模糊,好比你坐在桌旁想继续看你的书,无奈天色渐暗,光线不够——夜幕开始降临。为了再作点回忆,我不得不让自己的思绪稍息片刻,就像在昏暗的光线下阅读,你想再看几个字得先闭一下眼睛。该抹去的都已抹去,尚存的还有我纷乱的思绪,那是回忆的航迹上的泡沫或是它那芬芳留下的快感。然而,这种纷乱的思绪会自行消失,见到B夫人,我不再会激动。何必去对她说那些不为她所知的事呢?
唉!爱情就像这梦一般,带着同一种变颜改容的神秘力量在我心中逝去。同样,知我所爱,但没有出现于我梦中的诸君,请不要给我什么劝慰,你们是无法理解我的。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一百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他达到注定的某一级,预先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级,阶梯就从他的脚下消失,好像它是陷阱的盖板,而他也就消失了。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第二十级或是第六十三级,或是哪一级;他所确实知道的是,阶梯中的某一级一定会从他的脚下消失。
最初的攀登是容易的,不过很慢。攀登本身没有任何困难,而在每一级上从塔上的嘹望孔望见的景致是足够赏心悦目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新的。无论近处或远处的事物都会使你目光依恋留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物。越往上走,攀登越困难了,目光不大能区别事物,它们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同时,在每一级上似乎难以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也许应该走得更快一些,或者一次连续登上几级,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常是一个人一年登上一级,他的旅伴祝愿他快乐,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当他走完十级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后,对他的祝贺也就更热烈些。每一次人们都希望他能长久地攀登下去,这希望也就显露出更多的矛盾。这个攀登的人一般是深受感动,但却忘记了留在他身后的很少有值得自满的东西,并且忘记了什么样的灾难正隐藏在前面。
这样,大多数被称作正常的人的一生就如此过去了,从精神上来说,他们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地洞,那些走进去的人都渴望自己挖掘坑道,以便深入到地下。而且,还有一些人的渴望是去探索许多世纪以来前人所挖掘的坑道。年复一年,这些人越来越深入地下,走到那些埋藏金属和矿物的地方。他们使自己熟悉那地下的世界,在迷宫般的坑道中探索道路,指导或是了解或是参与到达地下深处的工作,并乐此不疲,甚至忘记了岁月是怎样逝去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时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和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时,他们会像阿基米德在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在人们眼前,还有一个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的广阔领域,就像撒旦在高山上向救世主显示的所有那些世上的王国。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永远感到饥渴的人,渴望着征服的人,人生就是这样:专注于攫取更多的领地,得到更宽阔的视野,更充分的经验,更多地控制人和事物。军事远征诱惑着他们,而权力就是他们的乐趣。他们永恒的愿望就是使他们能更多地占据男人的头脑和女人的心。他们是不知足的,不可测的,强有力的。他们利用岁月,因而岁月并不使他们厌倦。他们保持着青年的全部特征: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无论他们多么年老,到死也是年轻的。好像鲑鱼迎着激流,他们天赋的本性就是迎向岁月之激流。
然而还有这样一种工场——劳动者在这个工场中是如此自在,终其一生,他们就在那里工作,每天都能得到增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变得年老了。的确,对于他们,只需要不多的知识和经验就够了。然而还是有许多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他们了解最深,见得最多的。在这个工场里生活变了形,变得美好,过得舒适。因而那开始工作的人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熟练的大师只能依靠自己。一个大师知道,经过若干年之后,在钻研和精通技艺上停滞不前是最愚蠢的。他们告诉自己:一种经验(无论那可能是多么痛苦的经验),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察,一次彻底的调查,欢乐和忧伤,失败和胜利,以及梦想、臆测、幻想、人类的兴致,无不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益处。因而随着年事渐长,他们的工作也更必需更丰富。他们依靠天赋的才能,用冷静的头脑信任自己的才能,相信它会使他们走上正路,因为天赋的才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相信在工场中,他们能够做出有益的事情。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不希望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可能不会到来。他们不害怕邪恶,而邪恶可能就潜伏在他们自身之内。他们也不害怕失去力量。
如果他们的工场不大,但对他们来说已够大了。它的空间已足以使他们在其中创造形象和表达思想。他们是够忙碌的,因而没有时间去察看放在角落里的计时沙漏计,沙子总是在那儿下漏着。当一些亲切的思想给他以馈赠,他是知道的,那像是一只可爱的手在转动沙漏计,从而延缓了它的停止。
为了到花园里看日出,我比太阳起得更早;如果这是一个晴天,我最殷切的期望是不要有信件或来访扰乱这一天的清宁。我用上午的时间做各种杂事。每件事都是我乐意完成的,因为这都不是非立即处理不可的急事,然后我匆忙用膳,为的是躲避那些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并且使自己有一个充裕的下午。即使最炎热的日子,在中午一时前我就顶着烈日带着芳夏特出发了。由于担心不速之客会使我不能脱身,我加紧了步伐。可是,一旦绕过一个拐角,我觉得自己
得救了,就激动而愉快地松了口气,自言自语说:“今天下午我是自己的主宰了!”从此,我迈着平静的步伐,到树林中去寻觅一个荒野的角落,一个人迹不至因而没有任何奴役和统治印记的荒野的角落,一个我相信在我之前从未有人到过的幽静的角落,那儿不会有令人厌恶的第三者跑来横隔在大自然和我之间。那儿,大自然在我眼前展开一幅永远清新的华丽的图景。金色的燃料木、紫红的欧石南非常繁茂,绘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欣悦;我头上树木的宏伟、我四周灌木的纤丽、我脚下花草的惊人的纷繁使我目不暇给,不知道应该观赏还是赞叹: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争相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眼花缭乱,使我在每件东西面前留连,从而助长我懒惰和爱空想的习气,使我常常想:“不,全身辉煌的所罗门也无法同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相比。”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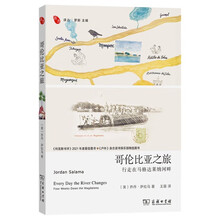




散文是最接近人类表达自己的一种形式,但在西方文学里,散文的定义首先就比较难下。英语里的prose(散文)的定义包括诗之外一切形式的文体,甚至小说。另一种散文形式叫essay,汉译名叫“小品文”,又译为“随笔”,也可称“论说文”和“杂文”。这种文体据说是法国著名文人蒙田的发明,此公现被界定为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和散文家。如果essay确系蒙田的发明,那么essay的发展至少也有四百年的历史了。这四百年正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外国文学各种流派充分发展的时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essay也算应运而生了。文艺复兴说来是“复兴”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学与艺术,但实质上是人类把自己作为主宰充分表达自己的过程。绝大多数文化巨人和学者,在画过画、写了诗、创作了小说和戏剧后,还会禁不住用essay写写自己,有些甚至写出了大名堂,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因此,包括essay在内的散文形式,在四百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可谓丰富多彩,精彩纷呈。从形式与风格上,本集子的文章都遵循化了这一准则,比如篇幅的长短,记述的形式,等等。
作为一个选本,选家最难做到做好的是内容方面的取舍:是偏重抒情呢还是偏重记事?是偏重思想呢还是偏重文化?绝对的界定是不存在的,但有所侧重是很需要的。本选本遵照了中国“文以载道”的说法,尽量让所选文章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不同一般。涉及思想与文化,自然离不开文化巨人的文章、研究和评论。本书中吴尔夫的莱斯利·斯蒂芬》、雨果的《巴尔扎克之死》、茨威格的《告别里尔克》、瓦萨里的《达·芬奇轶事》、普鲁斯的《萧邦故园》、格里格的《梅兰芳》、列文的《莎士比亚》、东山魁夷的《星离去》等等,都是写人论事的大手笔文章,都掘深刻,论点精当,引人思考:阅读这一类文章,读者得到的不仅是著名人物的身世,还有他们的时代背景和人类的生存理由,以及社会演变的轨迹。这类记人说人的文章,思想性占了重要比例。
另一类重要选择点是状物、游记、点评时世和专题专论,从而折射一种文化的内涵。这类文章有的写一样东西,有的写一个地方,有的写一段时间,有的写一段生平;例如兰姆的《古瓷器》、卡莱尔的《歌剧》、勃勒的《在期破场徘徊》、加德纳的《年轻的美国》、普里彻特的《与世纪同岁》、拉班的《吃老本》、夏多布里昂的《别了,法兰西》、大仲马的《猎狼记》、伯尔的《莱茵河》、桑塔亚那的《英国人的性格》、利科克的《牛津如我所见》、博尔赫斯的《书》、川端康成的《我的伊豆》和普列姆昌德的《这是我的祖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