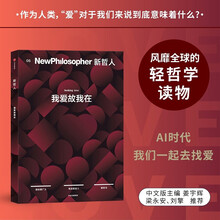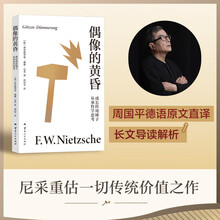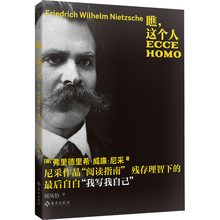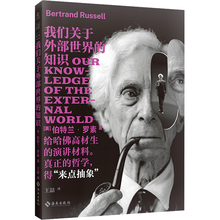虽然他在该书的前半部分坚持自己拥有作为中东人和巴勒斯坦放逐者的经历,他在英美学术象牙塔的特权世界里却几乎不是什么放逐者,而是那个俱乐部的正式成员,虽然是经常处于反对一方的成员。那个似乎要把他排除在外的俱乐部的这种布满荆棘的成员地位,或许部分地解释了萨义德何以有时无法明白,有关东方的东方学固定模式中的其他种种二元对立,为什么也会出现在东西方男人对妇女的固定模式当中。
由于萨义德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东西方妇女,所以他也就失去了使自己的研究方法对于各种不同的历史特异性变得更加敏感,并因此使它对东西方关系所进行的分析变得更加精确和全面的机会。而他没有认识到西方关于东方的东方学话语事实上远不如他经常指出或者暗示的那么统一而又占据主导地位,部分是因为他忽视了那些同东方有关联的西方妇女的生平和著作。特别是妇女的不少游记,同萨义德所认同的那种话语之间具有一种复杂而又易变的关系。因为,在萨义德有关东西方关系的阐释中,被删除的不仅有西方妇女,还有东方妇女。毕竟,东方妇女的境况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单纯地复制东方男人或者西方妇女的境况,它应该被纳入对东方学进行讨论的那种框架的理论化之中。公平地说,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概念上,要想做到这一点对萨义德而言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关于非西方妇女的文献,同或者是关于西方男人或者是关于西方妇女的文献相比,更不容易得到。对西方女权主义者而言,对非西方妇女的理论化显然也是微妙棘手的事情。这些西方女权主义者曾经受到过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等人的非难,指责她们把非西方妇女简化成了牺牲品的固定模式。这里,我自己的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了非西方妇女。最后,应该牢记的是,萨义德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对东方学话语的分析,而不在于非西方人对这种话语的反应。
尽管如此,对当代广告使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固定模式这一范例进行一番思索,分析为什么要在广告中纳入这些因素,还是颇值得玩味的。当今某些西方广告中出现的情况说明,与萨义德援用的阿拉伯人的那些粗糙的形象相比,这些广告在老到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表明,虽然某些广告部分地恢复了阿拉伯人充满色欲的形象(毋庸讳言,仍然是“酋长”那种固定模式化的人物),然而它们还是把东西方妇女降低为她们在传统上已被接受的固定模式化角色,即不同类型的性对象。在一则为驰名轿车做的电视广告中,两个金发碧眼的西方女人救出了两个汽车在沙漠里抛了锚的阿拉伯男人,其中一个阿拉伯男人,也就是酋长,感激涕零中对女人们说:“我的官邸也就是你们的啦。”西方妇女被酋长富丽堂皇的宫殿弄得眼花缭乱。不过,她们无意中听见酋长对自己得力的助手说:“它们[汽车]是我给妻妾买的。”(“Iwant them for my wives.”)她们把酋长的话误解为“我要她们做我的妻妾”,于是把酋长妻妾穿戴的那种蝉翼面纱和轻纱长袍穿戴起来,乔装打扮逃出官邸,匆忙驾车走了。这时,屏幕上出现了酋长带着会心的微笑,说:“我的话有什么不对吗?”与此同时,他的妻妾怀着赞美的心情簇拥在酋长给她们买的那些新轿车周围(自然,与那些西方妇女驾驶的是同一种型号的轿车),这样就说明,那两个西方妇女完全误解了酋长的话,认为"them"指她们自己,而不是轿车。这则广告是就阿拉伯人以及东西方妇女的固定模式所进行的有意为之的笔墨游戏。它先声明西方技术的优越,把阿拉伯人降至次要地位(他的汽车在沙漠里抛了锚)。不过又继而表明这位阿拉伯人所处的权势地位。那两个拥有以汽车为代表的技术的西方妇女,受到了有关东方生活和男女关系的愚蠢荒谬的假设的愚弄,同时还在心里夸大了她们自己的妩媚动人。广告中的东方妇女则是处于背景中的人物,身穿蝉翼服饰,轻盈地跑来跑去,被认同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男性想像中的性对象。她们不说话,别人也不同她们说话,她们只是那阿拉伯人权力和财富的标志。整个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西方男人的观点驾驭的,他是以汽车为代表的技术成就的假定发明者,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广告中所有的参与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