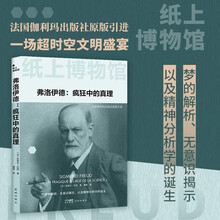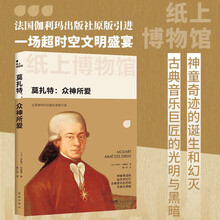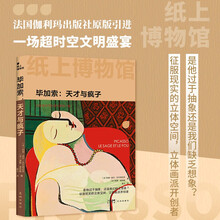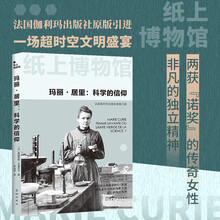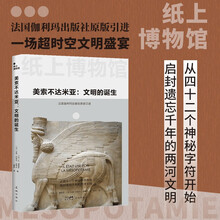我很快就从亲身的体验认识到,费米是喜爱体育运动的。
“我们必须赶快具体定下来。明天我们做一次短途的步行,后天走得更远一些。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爬山了,”当他出现在瓦尔加德纳时,他就这样说。他穿着一条灯笼裤和一件蒂罗尔式短夹克,比我第一次看到他时要自然些,不显得那么古怪了。
“我们到哪里去呢?”柯妮莉亚问道。她是个健壮活泼的妇女,是卡斯泰尔诺沃家的朋友、数学家莱维一奇维塔教授的弟媳。她劲头十足、滔滔不绝地说着,急得快要坐立不安了。
费米已经伏在一张地图上。
“我们可以到长谷去远足,一直爬到它的顶上去。”
“那要走多远的路呢?”吉娜问道。
费米把他那粗壮的大拇指按在地图上,移动了几次,量出了从长谷的底部到顶上的距离。费米的大拇指通常就是他的现成量尺。把它放到挨近左眼处,闭上右眼,他就能够测出一道山脉的距离,一棵树的高度,以至于一只小鸟的飞行速度。这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几个数字,随即回答了吉娜所提出的问题。
“路并不很长。大概每条路都是六英里。”
“六英里!这对于那些想和我们一起去的年幼儿童来说,岂不是太远了吗?”柯妮莉亚问道。在我们这伙人中,即卡斯泰尔诺沃一家连同表兄弟姊妹和各方面的朋友,包括有大大小小的少年儿童。家庭间的友谊远胜于在学校里结成的友情,这有助于避免美国流行的那种按年纪结伙的现象。
费米转过脸来朝着柯妮莉亚,用带着嘲讽的严肃神情说道:
“我们新的一代一定要练得身强力壮、耐苦耐劳,不要娇滴滴的。孩子们是能够走这样远的,或许还能走得更远。我们不要鼓励他们偷懒吧!”
再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经常总是这样的:费米提出建议,其他人就附和,在他面前放弃他们自己的意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