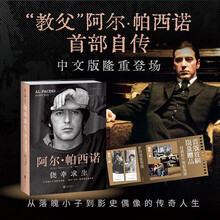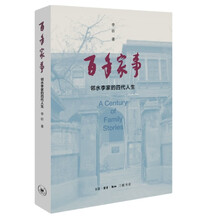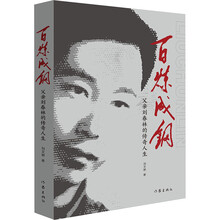柏拉图说,音乐深入灵魂内部并以最强有力的方式控制着它。为什么音乐会如此强烈地吸引我呢?是因为音乐,文化最纯粹又最神秘的表达方式,一上来就把我投入了这个世界的美化了的现实中?是因为音乐,当它达到最高潮时,其自身消失而把我们留在绝对面前?十一岁那年的一天,我看了一部克尔特神话风格的电影《神剑》,片中充满了华而不实的场景。不过瓦格纳的《帕西法尔》为这部电影预告片增色不少:当我听到这首乐曲时,眼前呈现的虽仍是根据导演的要求按部就班的一幅幅平淡无味的画面,但脑海中却叠现出一个个闻所未闻的世界,音乐赋予了它们色彩和层次,尤其是色彩,浓厚、强烈、配有图案。我第一次感知了一种具有神秘的本质、启示的力量以及普遍性的东西:如此,演奏巴赫的乐曲或者莫扎特的弥撒曲就是用音乐来描绘圣像。好几个夜晚,瓦格纳的这支乐曲纠缠着我,不断在我脑海里辗转反复。我痴迷地弹奏着钢琴,试图重现这支乐曲,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这首作品的简化谱。我悄悄地练习它,陶醉地弹奏它,沉浸在拥有完整乐谱的美妙幻想中。
音乐控制了我,因为它是寂静的延伸?在音乐之前的总是寂静,回荡在乐曲中的也是寂静。音乐是通往言语的他乡的途径,言语无法表达,而寂静却无声地诉说。没有寂静的音乐,不是噪音又是什么?
音乐就像是魔法,具有极为强大的诱惑力,它给人联想从而征服听众。如果说在古希腊神话中,音乐是众神的禀赋,只有神才能满怀热忱地演奏音乐,或者说音乐会施展魔法迷惑人,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美人鱼用她们的声音使尤利西斯偏离了正途,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还会让阿耳戈英雄们沉没大海。但是她们的歌声比不上俄尔浦斯的音乐,他的竖琴声可以驱散魔法。安徒生的小美人鱼也是以歌声吸引了她所爱的人。为了不让她嫁他,巫婆要她用声音来交换——多么吃亏的买卖!——迷人的双腿和优雅的步态。她失去了她的声音,失去了她的歌喉,为的只是能够迷住王子。 音乐又像是女人的香味,令人遐想联翩甚至神魂颠倒:她的香味是她的灵魂散发出来的神奇气味。那么女音乐家就以某种方式成了再生的美人鱼和恢复魔力的不灭的巫婆。只是,真正的男子汉不会答应屈服:科学、技术、理性使他免受迷惑人的外表的引诱。于是,当一个女人演奏或作曲时,她的音乐不再柔和甜美,不是俄尔浦斯和他的琴声,而是美人鱼和她们的歌喉,是为捕获而引诱的计谋。一切就在于此,就在这自古存在的重大对立中:一方是不吉的媚惑者美人鱼,听到她们歌声的人必然会遭遇风险;另一方是光辉卓越的神明俄尔浦斯,他的琴声不是令人着魔,而是迷人动听,给人救助……
因此,弗朗兹·李斯特在他的交响诗《俄尔浦斯》的序曲中描述了这位“歌曲之父”产生的力量:顽石点头、猛兽俯首、百鸟无声、瀑布断流,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艺术的超自然的祝福。俄尔浦斯给狮子挂上犁为人们垦荒,让豹子套上车供人们驱驰,引导汹涌的激流安静地带动水磨转动。天地万物专注地围绕在狮子周围,夜莺停止了歌唱,瀑布也不再低吟。这个使阿耳戈快艇下的狂怒波涛平息下来的人还催眠了科尔基斯的可怕巨龙,感化了动物、植物,甚至冥顽的哈得斯。
这位受神灵启示的歌手并不以鞭子来驯服巨兽,而是以琴声使它们信服。他以艺术和谐优雅的恩泽使无人性变得通人情。俄尔浦斯以他的音乐将人类引向了绝对的存在。而我呢,音乐改变了我,拯救了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