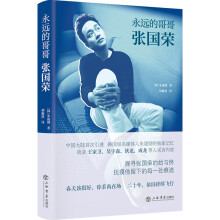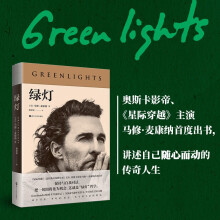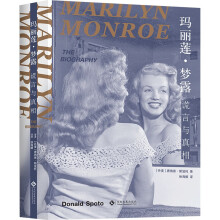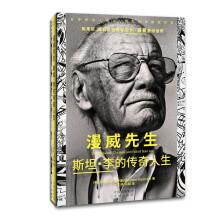小的时候,我的头发乌黑,我姐姐头发泛黄。人家叫我姐姐“小黄毛”,就叫我“小黑毛”。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黑毛”。妈妈忙于生计,爸爸又在遥远的新疆喀什,我较少受到大人的约束和管教。我的天性,获得了自由自在的发展空间。<br> 我常在家门口的桑树下玩耍,像一个小男孩似的,爬上桑树,摘取桑叶,喂养我的蚕宝宝。瞧着我的蚕宝宝们,在我的照料和喂养下慢慢长大,变得透明,吐丝结茧,又化成蛹蛾。我为这些小生命的演变感到异常的惊喜,也从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br> 我常跑到屋后的黄浦江边,看轮船在江上行驶,海鸥在江上盘旋,我望着那波浪滚滚的江水,流向烟波浩渺的天际,我的心也随着波光粼粼的江水漂向远方。<br> 我幻想变成一只海鸥,在江水之上轻盈地飘飞,披着透明的阳光,钻入白云蓝天之中,仿佛在蓝天白云之上,有人在向我召唤,我会随着它的召唤,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br>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就是一种命运的暗示,我终究要离开此地,飘泊在外,走向很远的地方,很远的目标。<br> 家门前不远处的小河边,也是我孩提时代经常光顾的地方。河畔的草丛里,有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在此起彼落地吟唱。春天,河里游弋着无数小蝌蚪,我用纱布、铁丝扎的网兜,在清澈的小河里捞蝌蚪。我把小蝌蚪装在玻璃瓶里,带回家,看着它们渐渐长大。<br> 夏秋之交,蝌蚪们就会变成青蛙,在我的家乡,管它们叫“田鸡”。入夜时分,田鸡在河畔呱呱呱地喊叫,像是在大合唱,我睡在家里都能听到它们雄壮的歌声。那合唱声,把我的思绪带到小河边,我会在童年香甜的睡梦中,变成一条小蝌蚪、一条黑色的小精灵,在我的家乡、在我家不远处的小河里幸福、快活地畅游。<br> 小河边的野地上,也曾留下我童年的踪迹。我经常挎着小竹篮,到野地上采摘野荠菜和马兰头。荠菜猪肉馅的馄饨是上海人喜爱食用的一种面食。我至今还能回味起我妈妈用我摘回家的野荠菜包的馄饨,那种散发出田野芬芳的鲜美。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味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上再没有如此美味的食品了。<br> 马兰头,也是江南一带的人喜爱食用的一种野菜。据慈禧太后宫女德龄的回忆,有一次,慈禧游逛颐和园,见到有几个宫女在摘野菜,便问摘的是什么,宫女禀告她摘的是马兰头,慈禧好奇,让御厨做这一道菜,试着品尝。不料,它让食遍天下美味佳肴的慈禧惊喜万分,居然连用数天仍称赞不已。<br> 我想,这世上任何人工制作的东西,永远也敌不过大自然的馈赠。我应该做一个像野荠菜和马兰头那样自然、质朴、本色的演员。任何矫情和做作,都不是一种好的演技。任何艺术的最高境界都是无技巧。<br> “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br> 可能,我毕生都不能达到这般境界,但我应该朝着这样至高的境界不断奋进,接近,再接近一点。<br> 我最初的梦想是将来长大做一个幼儿教师。从小我就喜欢带着一批比我小的女孩,玩“过家家”,像个导演似地组织她们担任各种角色。我常在家门前的大杨树下架一块小黑板,把这些小女孩召集起来,我给她们上课,教她们认字。<br> 后来我姐姐实现了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她现在就是一个小学教师。<br> 而我却出乎全家人的意料,被命中注定地引向了一条谁也不曾想到过的道路,成了一名职业影视演员。<br> 开始,我们全家都不支持我走这条路,我妈妈尤其反对我从事我现在的职业。<br> 为此,在我命运的转折关头,我和我妈妈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冲突,有关这方面的事,我在后面都会写到。<br> 在妈妈的心目中,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乖乖女,而像一个小男孩。<br>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黑毛,给家里摘野菜,算是我仅有的“善举”。我更多的时候是在外调皮捣蛋。<br> 我和我的几个表弟在家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路障,爬到树上去抓知了,穿着裤衩,光着上身,下到河浜里去摸螺蛳,到水田边掏蟛蜞。反正,男孩玩的事情,我都玩过。<br> 记得有一阵子,我和我的表弟常到野外的蔬菜地里偷摘邻居菜农种的菜,什么鸡毛菜呀、黄瓜呀、茄子呀,竟然还把偷来的菜堆在街上卖。那时我就像个民工的丫头,像一个小菜贩子,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却又不敢大声吆喝,结果当然是卖不出去,而又不敢拿回家,便送还给邻居,算址“物归原主”吧。<br> 我妈很少打我姐姐,却经常打我。她说我像个小男孩,太调皮。她们从小把我当男孩看待。我常在外惹是生非和闯祸。<br> 有一次,我和邻居家一个姓朱的女孩玩打仗,先是扔沙上、泥巴,后来又用煤砖相互砸,最后我把她的头砸破了,流了血。我害怕了,赶紧逃回家,躲在一张小铁床底下,像鸵鸟一样翘着自己的小屁股,认为别人就找不到了。<br> 妈妈回家后,把我从床下拖出来,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再拉着我,到朱家去赔礼道歉。但我并没有吸取教训,仍在外继续滋事。<br> 我像一个“孩子王”,像一个“女大王”,常带着几个小男孩,在我家门前几百米远的铁道线上奔跑、玩乐,看着火车从远处呼啸着奔驰而来,又望着它轰轰隆隆地驶向天边。我觉得乘火车远行,一定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我向往着有那么一天,我能搭上我家门前的那一列火车,让它载着我,把我带到远方,带到天涯海角,带到我梦幻的世界里去。<br> <br> 我第一次铰掉了长头发,把头发梳理成《血疑》里幸子的发型,希望自己像幸子一样得白血病,这样就能有人照顾,还能获得爱情,仿佛得白血病是一件时髦的事情。<br> 我穿上了流行的幸子裙,还用圆珠笔在自己手腕上点了印记,像电视里的幸子一样,逢人就说我得了白血病。我完全进入了幸子这个角色,还模仿幸子的神态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我的一张照片。<br> 这也许是我最初的表演,是我将来进入演员这个行业的一次最初的彩排。<br> 我像那个年代许多小女孩一样,专门为社会上出现和流行的各种歌星、影星定做了一本集美册,我收集了像周润发、刘德华,张曼玉、林青霞等许多明星的照片,贴在我的集美册上,并在上面写上我的评语和赞词。<br> 我向往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集美册上的明星。<br> 但我居住在上海的近郊吴淞地区,那里虽然有小桥流水、有大河奔流,还有桑树枣树什么的,却没有任何所谓的文艺气息,没有诞生一个当代影视明星的土壤和环境。<br> 前面我也说到了我的家和我的家人,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从事艺术的。所以,在我的家庭里,也并不具备诞生一个影视明星的条件。<br> 我的主要的监护人——我的妈妈,她和上海任何一个普通人家一样,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来呵护、哺育她的两个女儿。<br> 我姐姐和我越长越可爱,尤其是我姐姐,在学校里成了文艺骨干。小时候,她处处比我强,每次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她都上台表演,还担任报幕员。每当看到她在台上,穿着白衣白裙报幕时,我都特别自豪,会对身边的同学说:“这是我姐姐,你们有这样奸的姐姐吗?”那时,我幻想着有一天,也能穿上白衣白裙站在舞台上,受到姐姐和同学们的关注。<br> 那时候我还经常一个人坐在课桌前冥想,沉浸在自己美丽、缥缈的幻觉中。在这种冥想和幻觉中,我会成为一个像山口百惠一样的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成为一只凌空飞翔的白天鹅,成为一个骄傲、美丽的公主。<br> 我确实一天比一天长得漂亮起来,也开始引起班上男同学越来越多的注意。他们在私下里对我评头论足,却没有一个人敢靠近我、惹我。<br> 我开始发育后,从不和男同学说话。我不是一个在这方面早熟、喜欢招蜂惹蝶的女孩。恰恰相反,我是一个用红领巾捆扎日益发育的胸脯的刀枪不入的“圣女贞德”式的女孩,我在男孩面前的“大义凛然”,使他们对我望而却步。可当时我在班上又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因此这些讨厌的不安分的小男孩不甘心无所作为。<br> 记得有一次,也许我正独自坐在课桌前做我的白日梦,几个男同学在我身后点点戳戳,似乎在说,谁敢去和池华琼说话,谁敢去勾搭她。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后,其中产生了一个“唐璜”式的英雄,他鼓起勇气,走到我的身边,挨着我坐下。<br> 我不想理睬他,表面上仍正襟危坐,仍旧沉浸在自己的幻想的故事里。<br> 他嬉皮笑脸地搭了几句,见我没有反应,甚觉无趣,便企图动手动脚。<br> 这时,我突然伸手狠狠抽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那男同学惊呆了,旋即捂着脸,很没面子地跑开了。教室里其他同学也都惊诧不已。他们没想到我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如此地不近人情。过后没多久,班上的男同学就送了我一个绰号:冰美人。<br> 其实,我决不是一个他们所谓的“冰美人”,他们都不了解我,和我家人一样,他们都不了解我的内心世界。<br> 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自己向往的世界,那地方很远很高很美丽。但究竟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甚了了。我处于一种茫然混沌的阶段。<br> 我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我有着一个迷人的梦想。<br> 正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过的一本书叫《生活在别处》。<br> 我大约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吧。<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