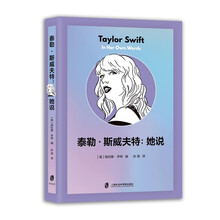背负子君的灵魂离家<br> 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br> 冰一样的柔情,我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br> ——盛英《梅娘与她的小说》<br> 1936年,梅娘十六岁。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世界上最疼爱她的那个人,她的父亲,因病去世。<br> 没有了父亲的家,对梅娘来说,仿佛一夜间从花的暖房,变成了寒冷的冰窖。家像墓地一样的空旷和死寂,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于是,梅娘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神户女子大学。<br> 这期间,梅娘是东京中国书店和内山书店的常客。她贪婪地、大量地阅读中国抗日大后方的书籍,她要像同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作家萧红一样,走文学创作之路。坚定的信念,不二的选择,天生的才气,奠定了梅娘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女作家的坚实基础。也许就在她下定决心的瞬间,一代杰出的中国女作家便诞生了。<br> 她酷爱鲁迅的文章,如饥似渴地读着鲁迅的全部著作。她觉得鲁迅的文章教给她观察人生、思索文学的使命,她的思想日益充实、成熟。此时,她认识了在内山书店半工半读的中国穷留学生柳龙光,两个年轻人一见倾心。这场恋情遭到了家族的强烈反对,并且以中断梅娘的经济来源相要挟,逼迫她放弃这段美好的恋情。不巧,此时同在日本留学的弟弟病重,需要人护送返乡。无奈,梅娘只得辍学回国。家人企图通过长时间的分离,使梅娘放弃柳龙光。<br> 强迫和分离对于热恋中的情人从来都是最愚蠢的做法,反而能更增加恋人间的思念和感情,梅娘断然拒绝了家里为她安排的婚事。一心等待心上人柳龙光回国与她团聚。等待的时光是<br> 难熬的,但也同时充满了希望和幸福。1937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柳龙光终于赶回长春与梅娘完婚,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家人依然不接受梅娘的选择,梅娘毅然同家庭彻底决裂。用她的话说:“我是背负着鲁迅笔下子君的灵魂离家的。”从此,梅娘走上一条新女性的自强之路。<br> <br> 梅娘是一棵散发着暗香的梅树<br> 我权衡者再,却怎样也不想离开这片被我血泪浸湿的热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热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br> ——《远方的思念》<br> <br> 有的人相处多年,分开后很快就淡忘了;有的人萍水相逢,接触不多,却会常常涌上心来。以笔名梅娘名世,岑寂了三十多年又重新被人们记起的女作家孙嘉瑞大姐,就是这样一位相见偶然,交谈不多,却难以忘怀的人。<br> 记得那是1994年三秋天,我们在加拿大探亲,应我女儿的朋友柳青女士之邀,去她家作客,见到了她年逾古稀的母亲,一位身量略显瘦削的老太太。她浓黑的眉毛透着刚毅,睿智的双眸仍很明亮;上身穿一件带黑色花纹的枣红色毛衣,下身着一条普通的灰蓝色长裤;神情安泰。女儿曾告诉我,她就是四十年代深受读者喜爱的有“南玲北梅”之誉的女作家梅娘。但相见之下没有半点名人派头。她说话轻声慢语,仿佛惟恐惊动了什么,使我原本有些激动的心很快平静下来。寒喧之后,聊些家常琐事。我称赞她的毛衣好看,她说摊头上买的,很便宜。还说,实在已不适合自己的年龄,太艳了;女儿鼓励她穿。我十分理解从灰黑蓝的大一统中过来的我们这一辈中国女人着装的顾虑,梅娘也不例外。看看加国老太太们越老越鲜艳的打扮,我们的观念是很该更新一下了。我们都说她穿着很合适,这年龄就该有点色彩。她欣然微笑。看得出,她脸上施了点淡妆,也就是涂了点唇膏。这在国外是一种礼貌,是女性应有的自爱自重,也是入乡随俗。<br> 近午,梅娘母女请我们到附近一家广东人开的翠醉楼喝早茶。各种粤式小点心、海鲜,花样不少,配上茉莉香茶菊花茶,吃得十分舒服开心,而要价不高。梅娘说这里的东西应该说还是价廉物美,老外来光顾的也不少,中国饮食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们初来加国,也感到这里的物质生活还是比国内好得多。很自然地想到她北京家中已无亲人,青年丧偶,一儿一女又在她最艰难的年月,于贫病中永远离她而去了。眼前的女儿是她惟一的骨肉,现在定居加拿大,生活相对优裕,完全有条件让历尽沧桑的母亲在自己身边颐养天年。我们劝她,不如就留在这里,与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女一起生活,彼此有个照应;这么大年纪了,身边没个亲人会有很多不便。老太太却极有主意,说那怎么行?还是要回去的,这里只是暂住;再说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家,也有不少朋友。柳青女士也无奈地说,妈妈是不肯在这里长住的。的确,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不宜单独居住的,怎么也该与自己的女儿相依为命,何必远离亲人,独自在空屋坚守苦熬?何况加拿大生存环境极好,多次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但梅娘却要舍天堂而去,她自有自己的想法:尽管能享骨肉团聚的亲情,但异国文化毕竟不是同一条根,许多方面无法认同,心理上难以调适,这是物质上的优越填补不了的。这番话说得我们颔首称是,无言以对。我感到了一个有操守有追求的老人对生存的理解,是不以物质生活的满足为目标的。她的天堂不在富裕的异国他乡,而在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故土,在自己心中。次年夏天,她还是回到了留下过她多少刻骨铭心的苦难坎坷和人情温暖的北京的旧巢,守护着内心那片曾是创痕累累却也风光无限的家园,用书和笔抵御着悄<br> 悄啃噬着她的孤独,与窗台上常被忘却而依然开得蓬勃的小花互通心曲,互励生之态的苍翠。<br> 当我们读了报刊上介绍她生平事迹的文章,得知她坎坷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不可想象的苦难,接连的政治迫害,无情的经济剥夺,惨痛的骨肉丧离,她却刚毅顽强地挺过来了,我心中不能不生出由衷的钦敬和无限的感慨,很想听听梅娘自己的说道。但梅娘却十分平静,认为没有必要再提过去的事。在我们看来,真是满肚子的苦水委屈,她却一句也没有倾吐,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真个是波澜不惊的样子。的确,荣誉盛名也罢,苦难也罢,少年曾享过的富贵也罢,后来经历的屈辱贫贱也罢,对她来说,沧海桑田,都已成为过去,都已化作生命的年轮。我感到了她澄明如水的宽阔的襟怀,和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自尊自强的人格的力量。她像一条蕴藏深厚的河,无语东流,不事喧哗,绝口不提自己。惟一言及当年的,是她曾赞扬北京女作家林徽因的才华美貌和过人的谈吐,以及文人学士交往聚会的盛况。我想她也该是参与其盛的,但她一句也没谈到自己。的确,今天面对的已是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生活,有多少值得她关注的新事物!她热爱生活,一种劫波度尽,欣逢盛世,而人已晚暮的紧迫感,使她重又拿起搁了三十多年的笔,小说、散文、译作,正像她一部作品的题名《依依芦苇》,散发着欣欣向荣的生命气息,这是何其可贵!<br> 这使我想起她1995年给我们的信中所流露的壮心豪气。“愿有朝一日,能大西北大东北地相聚北京茅舍,更愿脱一切框架,口无遮拦,聊个海枯石烂。”一颗洗尽铅华的坦荡的赤心透着何等大气!信中还说“我虽曾跑南闯北,但却无缘领略新疆风光,很想有机会让女儿陪伴到新疆一游。”豁达豪迈之气令人感佩。使我们深感抱歉的是,作为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我们未能及时促成此愿。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北京新疆的距离正在缩短,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我们殷切地期待着这一天。<br> 梅娘极重情谊。随信还寄赠我们三篇已发表的短散文。见文如见人。文中都触及她的身世、情怀,深厚凝重,而又体察入微,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咏赞生命的坚韧;不屈的痴情闪着永远的美丽光辉。<br> 梅娘永远不能忘记父亲的豁达、机智、富于开拓精神。要找男人,就要找像父亲那样的男子汉!所以,当她遇到性格与人品上颇与父亲有些相象的柳龙光时,便自然而然地一见倾心了。<br> 柳龙光同情共产党,心向抗日力量。进步作家李克异(电影《归心似箭》的作者,又名袁犀)被关东军逮捕后,经柳龙光多方营救,始得出狱。他还利用在日本当记者的身分,与朋友一起秘密地替新四军买药,陈毅同志曾亲笔写信表扬他们的爱国热忱。1948年主持城工部工作的刘仁同志,命柳龙光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去作当时蒙疆政府的参谋总长乌古廷的转化工作,争取乌古廷起义。为执行这项任务,柳龙光偕梅娘一起到了台北。但乌古廷在此之前已转到蒋介石一边去了。柳龙光在台北接到刘仁转来的口信,命他速返上海。于是,柳龙光应召去了上海,梅娘在台北等他。谁知,柳龙光在从上海返回台北时,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难时年仅三十岁。<br> 仅仅八年的夫妻生活就这样突然中断。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青年丧偶!<br> 柳龙光走了,留下了两个女儿。梅娘怀着身孕从台湾回到上海,柳龙光的遗腹子是个儿子。看着儿子,梅娘一遍又一遍地咀嚼青春丧偶的痛苦。她顽强地活下来了,她要带好三个孩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