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滔滔,水天一色。
自19世纪后期起,往来于中日之间的轮船就不绝于途;或经商,或求学,或探亲访友,或亡命海外,等等。颠簸之中的人们怀着希望和憧憬、惆怅和无奈……
此刻的苏曼殊,正与嫡母黄氏及舅父黄玉章乘海轮向广东家乡进发,同行的还有庶母大陈氏之女苏惠玲。随着海浪的起伏,尚懵懂不甚了事的苏曼殊的大脑正在拼凑着家乡的模糊图景。船中的各色人等带着不同的表情,在他的眼前晃动。从小就欢喜在纸上涂抹的他,目光投向了一艘迎面驶来的汽船,情不自禁地索要纸笔画了起来。
回到祖籍所在,应该说是苏杰生和黄氏的主张:逐渐长大的三郎已经到了就学的年纪,他的根基在中国,祖先的在天之灵会召唤后代们回到华夏大地、回到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的故乡。
祖父苏瑞文、祖母林棠,对于在遥远的异乡出世的孙儿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老非常仔细地从上到下打量端详着苏曼殊:“阿戬这孩子的身体里流着东洋人的血呢……”这样想着,但眼光里还是流露出了慈祥及宽慰:这孩子毕竟是咱苏家的后人。
离开了母亲的苏曼殊完全被笼罩在与日本横滨不同的氛围中,到处都能遇到新奇的甚至带有怪异的目光;他觉得自己差不多成了村子里最引人注目的人了。由别人直直地注视的感觉可不怎么好受,而这样的眼光又几乎无法避开。如果在日本,他可以躲人母亲宽广的怀抱,母亲会给儿子精神和心灵上的翼护。而眼下,周围的自家人,从祖父母到兄妹、叔婶,有的亲近,有的疏远,谁又能无微不至地觉察出他心底的不安、惶惑呢?很快,被冷落的感觉产生了。苏氏是个颇大的家族,年纪和苏曼殊差不多大的孩子有一群。看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兄弟姐妹们,
父母在一旁的叮嘱及呵护,疼爱的脸色,他的鼻子不由发酸。于是,河合仙那熟悉的微笑的面庞不时地浮现。
更令人心寒的也许是那种视之如“杂种”的不屑神色与窃窃私语。在归国之后的多年里,苏杰生的其他侍妾天然地对他抱有敌意。年少的苏曼殊忍受着孤独寂寞的煎熬,他孱弱的身体实在不堪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他的言语一天一天地少了,即使有人逗他说话,他也往往心不在焉。沉默往往是此时的他唯一的举动。
幸好,在简氏大宗祠村塾的读书时光给苏曼殊带来了一些快意和安慰。塾中同学有他的两个叔叔和兄妹们,其他沾亲带故的也不少。大家常在一起多少抵消了他的孤寂感。读书之佘暇,还与长兄苏煦亭、堂兄苏维翰等到野地里游玩,孩童调皮的天性又回到他的投手举足中。他甚至还不时地戏耍自己的兄长,于是,在兄弟间的手舞足蹈的嬉闹的混乱中,苏曼殊暂时地忘却了烦恼和苦闷。
苏曼殊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塾师苏若泉赏识这个学生,也一直给予勉励,因而,自家的弟兄姐妹们不由不刮目相看。
村塾所教授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小学和经史,也有一些文学知识,如诗词的诵读、联句作对等。从苏曼殊的知识结构来看,诗歌与近似于小说的笔记类作品的分量较重。其妹惠珊后来回忆说“三兄曼殊素爱文学”,并且小楷书写端正整齐。绘画尽管非塾中所授科目,苏曼殊依然乐此不疲,一幅幅画被堆叠在家内的书柜里。他的这位妹妹受到感染,也欢喜“选读三兄所读过的书”。
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而言,苏曼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塾中六七年只是起始的一步,他日后的文学业绩,是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求知,不断汲取新知识、新学理而获致的。但是,传统意识在其作品中的表现仍然是确实而明晰的。
1892年(光绪十八年),已经九岁的苏曼殊正埋着头在书籍中巡阅,忽闻听父亲从日本归来的声息。
与广东故乡睽违已久的苏杰生满怀沮丧,他在日本的经营活动失败了;如不打算另谋出路以改变现状,以后在日本的生计将愈益艰难。随他一起回乡的还有他两个妾大、小陈氏及几个女儿。除了河合仙,苏杰生中国血统的妻妾们都已归至故土,而且,此后苏杰生再也没有重返日本。
与父亲本有些隔阂的苏曼殊的眼光在父亲脸上只停留了片刻,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还避开了庶母有些威严的盯视;两个妹子带着好奇对小哥哥瞧个不已。苏曼殊茫然而又怀着企望地将目光朝别人的缝隙间探究,“我的妈妈呢?……”
村塾中的读、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继续,苏曼殊的心中多了些许伤感。他隐隐约约地觉得母亲与嫡母、庶母是不同的,否则她为什么让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儿呢。祖父母,还有几个大人有时也会问寒问暧,但他们无法取代母亲的挚爱和悉心呵护。
苏曼殊深深地思念起远隔重洋的母亲来,恍惚中,母亲轻轻抚摸自己的头,柔柔的声音令人心醉:“三郎,妈妈来了……”
幻觉过去之后,苏曼殊陷入哀伤: “我是日本人,我的妈妈也是日本人,所以……”
在日本东京和生母河合若及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一段时期,老人为三郎取了个日本名字,叫“宗之助”。在广东地区,即使有中国血统的父亲(母亲为外国人)、即使相貌与国人无异,也被称作“番鬼仔”,或以“杂种”咒之。苏曼殊自认是日本人,未必是因为他不清楚父亲为中国人。
父亲对儿子的关爱本来淡薄,但与父亲的团聚毕竟使孤寂无依的心有了一点倚靠。父亲偶尔也会说些你妈妈在日本如何如何的话,可是苏杰生的脑子更容易被生意占据:家中一大堆人个个张着吃饭的嘴,商业都市上海正诱惑着商人苏杰生的本能。回到沥溪两年多后的1895年,他即远赴上海再次从事他的经营本行,同往者是庶母大陈氏及其女儿;长兄苏煦亭则被遣至日本横滨习商,苏氏家族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延续是维持整个族人的生计所必需的。苏曼殊一生似乎未曾涉足此道,然而,他离家独自生活的费用有时也仰赖家族。
父亲的离去,可能给苏曼殊内心造成了恐惧,他由此而得了一场大病,并险些送命。于是,就在苏杰生赴沪的下一年,忧心忡忡的姑母苏彩屏将侄子携至上海父亲处。
大陈氏的裙边有一群女儿,但未生一个男儿,对苏曼殊怀有天然的嫉恨和不满。她用手直指:“你、你这个不知哪里来的杂种!”有时大声叫道:“滚回你日本臭娘们那里去吧!”她眼里透出的神气常使这少年不寒而栗。而苏杰生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再说,他也无暇为此事而分心。对慈母河合仙的温馨安详的回忆常使苏曼殊入神,而当下,庶母的淫威引起了他内心的惊恐不安,这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的强烈而鲜明。体弱少年的心灵岂能忍受这样的重负和压抑?
这一时期,少年苏曼殊的命运是坎坷的甚至是不幸的,这不能不影响并左右他日后的人生历程,使他的人生观染上了揉杂的灰暗的色调。当他投入到那嚣扰纷繁、五光十色的大干世界中去的时候,所经历的多忧少乐的情形像幽魂一般挥之不去,各种景象会浮现出来压迫、缠绕他的心胸。
上海期间,一个外国人,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Lopez Johnson即洛佩兹,约翰逊)进入苏曼殊的人生。这是苏曼殊了解、掌握英语的开始,英语为他展开了一个新天地,步入这个天地徜徉游览,显然使苏曼殊受到了一次洗礼,为他人生的精神及心态楔进新的因素。他和这位牧师的情谊有点不同寻常,可说具有神交的意味;虽然相识一年多之后苏曼殊即赴日本游学,但以后的相晤或书信往来都会使他产生快慰与兴奋。
与刘三同游古城,谈笑风生者是刘三,苏曼殊之长不在口说,但他对于种种胜景之奥妙实能默会了然于心,他也以画家之眼流览赏会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
二人在古城名胜鸡鸣寺逗留,并登上鸡鸣山北极阁观望寺北的台城和玄武湖。苏曼殊的目光由近而远,由远而近,沉浸在思古之幽情中……自东晋以来,玄武湖就成为一方胜地,湖中有洲,游赏之人不绝;南朝君臣,以湖水为演武之所,而洲中黄册库又贮藏着天下之典籍。台城与玄武湖相接,所在之处为南朝时的宋、齐、梁、陈宫殿遗址,更早本为三国时吴宫之后苑。台城宫苑的废墟中,蕴藏了无数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这里,我看见了历史的真谛……”苏曼殊百感交集,似乎是自言,又像是想得到刘三的应和。
“沧海桑田啊,不过,遗址犹存依稀,正待吾辈来凭吊呢。”刘三说时,朝苏曼殊瞥了一下,只见他眼神凝重,心里不由一动。一回住处,苏曼殊绘成《登鸡鸣寺图》,题文中情不自禁而又郑重地写入“百感交集,画示季平”等字。
苏曼殊对鸡鸣寺一游生情。登鸡鸣寺环望,东有紫金之山耸立,幕府之山巍峙于城北,茫茫玄武湖水正在眼下不远,沿湖西南岸城墙无声地逶迤。这一切,都使登寺带有更浓厚的兴味。苏曼殊还应本地人氏伍仲文之邀,复作鸡呜寺之游。伍仲文记其时游兴:两人携杖比步,“且谈且行,意至爽适”,登高后,远眺近瞰,大有“荡涤尘怀”之感,随即是“纵谈往事”,好不快意。二人的游兴还通过联诗抒发:
赫赫同泰寺,萋萋玄武湖。(曼殊)
红莲冒污泽,绿盖掩青菰。(仲文)
幕府林葱蓓,钟山路盘纡。(曼殊)
苍翠明陵柏,清新古渡芦。(仲文)
天空任飞鸟,秋水涤今吾。(曼殊)
六代潜踪汉,三山古国吴。(仲文)
悠悠我思远,游子念归途。(曼殊)
掉头看北极,夕照挂浮图。(仲文)
伍仲文与苏曼殊在日本时,同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此番重会,使苏曼殊羁身金陵的日子多了几分愉快的心情。同泰寺是鸡鸣寺的别称,二人联句,旗鼓相当。苏曼殊“天空”一联和“悠悠”一联,主观意绪的流露较为显豁,着眼点与伍仲文有异。“游子”之思中,还多少掺和着无家可以栖身的辛酸。苏曼殊的诗歌多短句,此则排律格式,尽管长度有限,当仍费思量。
苏曼殊在南京结识了清政权新军第三标标统赵百先。赵百先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求学时即痛愤清廷腐败:东游日本,得遇黄兴,后于1911年与黄兴分别任革命军正、副司令共同领导广州黄花岗之役。此前,他曾谋划在保定新军秋操时起事,未成,复回南京。标统任上,他援引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等人新军任官佐,并参加同盟会。苏曼殊深为赵百先的豪爽的气概倾倒,他在随笔中记述当时相得之状:
每次过从,必命兵士携壶购板鸭黄酒。百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歌于风吹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也。别后作画,请刘三为题定庵绝句赠之曰: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 负尽狂名十五年。”
苏曼殊刚晤赵百先时,即断言其为“将才”。赵百先一生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其作为反清革命志士的军事筹划和策动工作。显然,苏曼殊对赵百先的“豪饮”、“高歌”之风釆也不无倾羡之情。从忭格及举止而言,赵百先与刘三倒有些相似,“狂名”,二人可以当之。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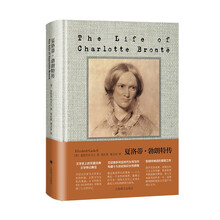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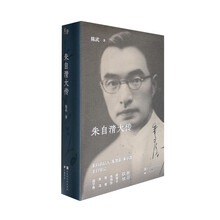



情僧与诗僧苏曼殊
苏曼殊,是个一生都和情产生不解之缘的诗人,同时又是终身以佛陀为人生皈依的僧人。
他短短三十五年的生活历程,是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的动荡中度过的。乱象频生,苏曼殊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牵人动荡漩涡的中心或接近中心的边缘,成为众生所瞩目的人物;而他内在的情感世界,既欲远离沸羹蜩螗的现状,又对民生国事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人生即是矛盾,对于苏曼殊来说,似乎更有实际的缘由;然而,他遁迹佛家之清静的精神苑囿,不仅是为了消解、对抗昏暗浊世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并且也有与生俱来的因而是难以解脱的宿命的推力。
寻花问柳的行径,是苏曼殊意欲避世以求慰藉的另类举止:灯红酒绿和轻歌曼舞令人迷醉,那些善解人意的女性,能给苏曼殊带来他人无法替代的温情及刺激。在这个诚心向佛的“和尚”、“大师”眼里,妓女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他在海外乃至病重时,还念念不忘上海的那一群可人的年轻女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家如此说,苏曼殊是否也以此作为支配自己的为人和行事的意识呢?由于他终身未娶,又自幼缺少家庭的关爱,因此,对女性的兴趣和钟情,是心理上的——种自我补偿。
苏曼殊的本性是诗人,只有诗歌才能承载和化解个人的真实的丰富的感情。
他的诗歌(还应包括绘画)使他生命的存在个性化和艺术化了。从古典诗歌的源流上看,其风情和格调远契中、晚唐,近则得益于龚自珍;—一些诗篇弥漫着伤感及哀怨,无疑,这是其一生依止不定的流离生涯的投射,也是对于男女之性爱的欲离还即、欲即还离的矛盾情感的显露。豪迈硬朗之气的匮乏,似乎和他的革命意志相背,但这恰恰表现了苏曼殊诗歌独特的内向性。换言之,他写作的情态就是精神上的内视反省,寻愁觅恨。